宏文怀旧系列散文之二十一
倔强的二哥
文/孙宏文(广东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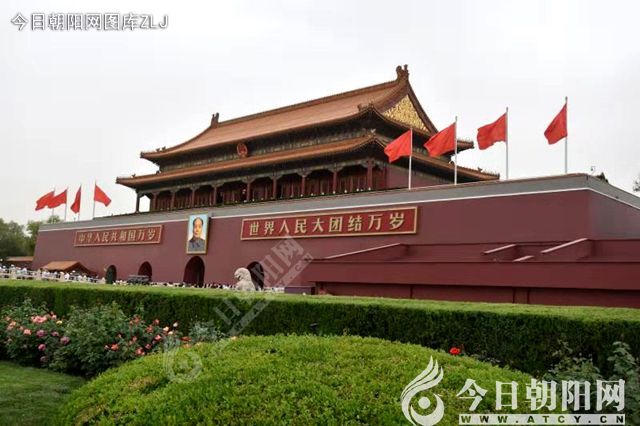
2012年的1月22日是除夕,这天下午三时许,住在海南的我收到二哥的儿子大伟的电话,说他爸住院了,并处于昏迷状态。大伟的电话过后,我心里惦记二哥,就拨回电话询问了几遍病情。大伟回答说:“一直昏迷不醒。”
此后,我心里一直不安。正月初二晚上,四弟洪武打来电话,说二哥病危,正准备后事呢。为此,一直有睡觉就关手机习惯的我,竟一夜未关机,也一夜未睡安稳。心里恐惧着,怕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凌晨五时,手机响了,我迅速拿起来。四弟洪武哽咽着说:“二哥已经咽气了。”虽在意料之中,但听到这消息,仍掩饰不住悲痛,顿时眼泪流了下来。因为我身在外地,在二哥去世时竟未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此时,二哥的音容笑貌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二哥的一生,是亦家亦工的一生,是艰苦倔强的一生。
二哥名叫孙洪彦,在家兄妹五人中排行老二。二哥长我四岁,当年应为68岁。许是先天不足,许是生活困难所致,二哥个子长得矮,大约一米五六吧,是我们家五兄妹中最矮的一个。二哥个子矮,小时候身子也很单薄。在我十几岁时曾听妈妈说过:“你二哥小时候,人小胆子也小,走路连一个小小的水坑都不敢迈。”二哥人虽然长得瘦小,但他既精明又很聪明,也很有才气。他不是手高眼低的人,是手笔相随。念书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优秀生,一直是学习委员,尤其是文科,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他的作文一直是学校范文。
二哥念中学时是在朝阳市第七中学,校址在朝阳县十二台公社。二哥念中学离家二十五里地,是自带粮食的住宿生,在校时大约每个月回一趟家往学校背粮食。想一想就知道,扛着粮食走二十五里河套路是什么滋味,那受的累不说也明白。二哥在中学念了三年,临中学毕业考高中时,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都说:“孙洪彦考高中很有把握,谁考不上孙洪彦也能考上。”可是,老天却偏偏开了个大玩笑,发高中录取通知书时,老师认为考高中没有希望的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二哥等到录取通知书发完,录取生上学了也没接到录取通知书。这时二哥明白了,自己没考上。学校老师和我的父亲感到意外和困惑,也深感惋惜。对此,父亲也曾张罗着去县教育局给查查分,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父亲也就是在家说说,可能是给二哥一个安慰吧,过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哥在中学念书时,记不清是1961年还是1962年放寒假,二哥把在校没有吃完的20多斤粮食扛回了家,那么远的路,累的程度可想而知。二哥扛着谷袋子到家墙外时,我正在路边玩呢,时间也就是上午十点左右。我见二哥扛着粮食袋子就赶忙去接,也许是扛得太久扎袋子的绳子松了,也许是我手没抓紧袋子口的原因,袋子口的绳脱了扣,谷袋子掉在了地上并撒出了很多谷子。此时,二哥很来气,什么也不说,带着气沉着脸,抬起脚就踢了我一脚,他的意思我明白,他都扛到家了,让我给整撒了。我自知理亏,什么也没说,赶紧回家拿来扫帚和簸箕把洒在地上的谷子收起来。在那困难的年代,粮食比金子还贵呀!
二哥中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二哥念书的那所中学。开学那天,爸爸在生产队借了一头毛驴驮上行李,二哥赶着毛驴把我送到学校。当年寒假,也是二哥牵着毛驴来到学校把我接回家的。记得二哥接我那天,学校食堂吃饺子,二哥和食堂大师傅挺熟,免费让我们哥俩吃了饺子。
二哥毕业没有复读就回家当了农民,可能过了一年左右,二哥便当上了生产队长。1964年搞“四清”运动,“四清”工作组看二哥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就准备把二哥送出去培训,培训后参加外地“四清”工作组。当时大队领导不同意,说我们要培养孙洪彦做大队后备干部。培训没有了,二哥就到大队当团支书。在二哥当大队团支书时,公社领导又让二哥去公社当团委书记,大队领导也是没放。两次机会,二哥都没有走成,也就走不出农村了。可能是命运的使然,二哥在大队当团支书值班期满,接到公社一个通知,让大队选3名条件好的青年进行体检,到地区汽车大修厂当合同制的轮换工。二哥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并通过了体检。二哥从此由农民当了工人,由农村进了城市。
二哥有才气,口才也好。他在汽车大修厂当工人期间,很有名气,发言不拿稿,这是以后我在大学念书时到大修厂时听说的、见到的。那是1976年,我大学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常常去大修厂看望二哥。有一次,我在二哥宿舍里,他让我帮忙写篇发言稿,一会儿厂子开会用,并为我找来一张报纸作参考。约一个小时多,二哥回来问我写完没有,我说还没写呢。二哥说现在写也不赶趟了,不用了,我不用稿子也能讲一阵子。我当时很汗颜。
二哥结婚在老家,嫂嫂是农村户口,当时叫亦工亦农。所以,二哥就把家安在了农村老家,在厂子一直住单身宿舍。二哥住单身宿舍,为我提供了方便。我在城里考大学,体检的五、六天里,我就在二哥的宿舍吃住。我每去一趟,二哥总是把床铺留给我,自己去外边找宿舍住。我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虽然同二哥在一个城市,但由于工作忙,特别是结婚成家后,就很少去大修厂去看望二哥了。
可能是在1983年,二哥得了病,爸爸和嫂嫂陪他到沈阳、天津和北京看病。医院大夫说想啥吃啥吧,时间长不了。大夫说过之后,爸爸和嫂嫂陪着二哥无奈地回到了家。到家后,二哥抱着一线希望看中医、吃偏方,奇迹竟出现了,病情逐渐好转起来。虽然病情有好转,但二哥一直在家养病不能上班,为此办理了病退。二哥年轻时没干多少农活,也没在农村受多少累,可在家吃药养病的日子里,二哥是一边吃药养病一边干农活,一家四口人的口粮田他全包了,从春种到秋收没有闲的时候。这样,一直干了30多年农活,直到去世。这三十多年,他也陪伴了孩子,一儿一女也都长大成人,分别成家立业。他暝目了,他无虑了,泰然地走了。
二哥这后半生,把没做过的农活都做了,把没受的累受了,把没受过的病痛的罪也受了。他是先轻后重,先甜后苦。其实,二哥没享过福,自己没单独下过饭店,更没有在饭店甩过大盘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过着普普通通的、不缺吃少穿的农家生活。二哥的一生,吃穿极其普通,吃的是农家饭菜,过的也是农家自给自足、自耕自食的日子。在穿戴上,二哥当工人时,在家总是穿着工作服,没置办过时兴的高档的服装。二哥在家养病为农的日子,我见到二哥总是穿着一身兰制服上衣、青色裤子。除冬天外,总也不戴帽子。
二哥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怀才不遇、不能得到发现是没有遇到伯乐,也是自己正直和性格倔强所致。这些可能是他终生的遗憾。
二哥的一生,没有特殊的爱好。烟是过路烟,在抽与不抽的两可之间,扑克、麻将也都会。那么精明的人能不会玩吗?但他不爱玩。他曾和我说过玩物丧志,当农民玩上了瘾,会耽误农活的。
我还记得,2010年夏季,我从海南回家来去妹妹洪珍家,我和二哥、四弟睡在一个大炕上,哥仨睡在一个大炕上已经是四十多年没有的事了。在火炕上,我和二哥拉家常说旧事,唠嗑到后半夜。记得当时,我当笑话谈起洒谷子挨了一脚踢的事,问二哥是否还记得。二哥嘿嘿笑着说:“咋不记得。”我又怎能忘记,见二哥最后一面是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我老伴儿周年祭上。
时隔两个月,二哥就匆匆走了。虽然我的心情很沉痛,但是按二哥先前得病仅能活数月的医生诊断,恐怕在三十多年前就离开了我们。二哥硬是用他那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战胜了病魔,又陪伴家人和亲人三十多年,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助编 繁花似锦 责编 立军]


 家有贤夫(杨秀兰)
家有贤夫(杨秀兰) 人生是一场修行(晏春华)
人生是一场修行(晏春华) 在阅读中遇见最美的自己(晏春华)
在阅读中遇见最美的自己(晏春华) 考场外的守护(唐士超)
考场外的守护(唐士超) 挖野菜(李文静)
挖野菜(李文静) 瓢虫之死(孙玲玲)
瓢虫之死(孙玲玲) 母亲的菜园(李文静)
母亲的菜园(李文静) 民间故事丨意外(王庆民)
民间故事丨意外(王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