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炕情话
文/尤来顺(辽宁喀左)
东北人住土炕,我就是在土炕上诞生的。房子是土坯房,炕是土坯炕。老人讲,沟沟壑壑房相似,家家土炕却不同。但在我眼里,家家户户的土炕却是一模一样的:土炕占据东屋与西屋的一半空间。东屋的土炕用来住人,西屋的土炕用来摆放农家杂物。老人说有的人家的土炕能够通烟顺畅,有的人家的土炕整日倒烟,有的人家的土炕五年不坏,有的人家的土炕不到一年就倒塌。
小村里有一个不成文的祖训:自家脱自家的坯,自家盘自家的炕。换句话说,自家的土炕,不能找外姓人来盘。我们家的土炕一直都是爷爷给盘的,通烟顺畅,冬暖夏凉。别看我爷爷只是个普通的铁匠,却绝对是个盘炕大师。很多外姓人都羡慕我爷爷的手艺,就是学不会。
村里若来皮影戏班子,都争着去我们家里住。尤其是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盆,特暖和。父母干脆把西屋的土炕收拾一下,让客人们住东屋的土炕,我们一家则住在西屋。就因为这,每次皮影戏班子准备离开时都会加一宿戏。这让村里人很感动,进而对我的祖父及父母也是满满的赞许与感激。
要想盘炕,少不了脱坯。脱坯不但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令人感到很意外的是,在我们村脱坯这种累活都是由家庭妇女来固定完成的。东北多是黑土,离地面两三尺的地方才能见到黄土。黄土性粘,加上麦子秸,做成的土坯劲道耐用。妇女们穿上男人的衣服,撸起袖子,哈口吐沫于手掌,搓吧搓吧就开始上手。和大泥,脱大坯,该用力时用力,该弯腰时弯腰,那身手,比一个好老爷们儿都利索。脱好的泥坯,要在太阳下暴晒十天之后才能用。
老马家的一个儿媳妇是最能干的,我们都叫她马二婶。她脱的土坯能够搭二十铺土炕的。那些土坯工工整整地摆放在院子中,像一座小山。
那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听说谁家的土炕塌了。我和很多小伙伴可以聚在一起,在老马家或老张家的院子里爬树上墙地耍弄。从那倒塌的炕洞里能散发出一种刺鼻的草木与泥土水乳交融般的香味,让人着迷。打着哈欠的男人顺着窗子将陈旧破碎的土坯往外扔,妇女则忙着将晒制好的坚硬的土坯往屋子里运,盘炕人手里拿着铁家什,嘴里含着冒烟的旱烟,坐在窗台上一声不响。盘炕人多是家族里年纪最长最有声望的老人。盘炕的过程是严肃的,但那只是大人们关注的焦点。孩子们的关注点是土炕盘好后,他们会被主人家请上土炕,尽情地蹦跳,看谁跳得最欢。跳得最欢的孩子会得到一种叫“花生占”的吃食,好吃极了。村里人管这叫跳炕,一是可以增加土坯之间的稳定度磨合度,再就是可以看看哪块土坯不结实且有了裂痕。如果孩子们蹦跳一段时间后,那土炕没有异样,说明这土炕盘得好。接下来,孩子们可以继续在院子里玩耍,盘炕人优哉游哉地给土炕抹泥挂面。其实,抹泥挂面也是个颇看功力的活。盘炕人不用尺子,只凭感觉,就能把炕抹得溜平。主人家在外屋的灶火里用麦子秸生起火,那带有麦香的烟雾在土炕内耍玩一圈后,沿着灶洞,通过烟囱,缕缕升腾,飘向太空。待灶内火苗越着越旺,便放上硬柴。村里人见到升起的炊烟,就知道又一铺土炕诞生了。
灶内生火,一是可以加快新土炕干燥的进程,再就是可以在铁锅内炖猪肉。那肉是用来款待盘炕人的,也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毕竟,我们对那座新土炕的形成是出过力的。那种炖肉的味道,即便是我后来离家多年,嘴角留有挥之不去的余香。
土炕也叫火炕。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屋内却异常温暖。村里的孩子们几乎都是光着屁股在土炕上度过一个个冬天的,我也不例外。夜里,月光透过窗棂洒入土坯屋内,静谧而温和,我躺在暖乎乎的被窝里,一边听妈妈讲故事,一边想马家二婶家来的那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穿着花格子外衣,梳着两个小辫子,辫子上还有红色的头绳哩!我妈说:她是马家二婶娘家的小侄女,从城里来的。几天后,我和那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因为我家的土炕是出了名的好,她还在我家住过好几宿呢。
土炕不但可以用来睡觉休息,也是我们吃饭或款待客人的地方。饭桌一放,无需椅子,一家人盘坐在土炕上,有说有笑。热了,索性脱掉外衣,甚至光起膀子(特指男性)。冷了,可随手扯过被垛上的一个毯子往身上一披,接着吃。有时,我和弟弟因为抢夺埋在菜盆里的一块肉而斗智斗勇,父母则在两边各自充当我们的军师。最终两兄弟也都是化干戈为玉帛,大笑起来,继续吃饭。偶尔,也希望家里的土炕上多出几个客人。农村有习俗,客人自然要在我们家吃过饭才离开。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些长辈们留下的剩菜剩饭,那味道非常香,依然有肉,像过年。
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家的土炕上也时常有来串门的村里人。他们和我们父母唠家常,谈庄稼或节气,一壶茶水可以喝一天。
八十年代末,我家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是村里的第一台彩电。不管白天黑夜,土炕上的人更多了。为了看《封神榜》,有一年,我们家的木质窗户愣是让人给挤破了。弄得我在自己的土炕上没有个安稳的容身之地,但心情一直都很美。
去县城念书,开始住床,很不习惯,但也没有办法。床没有土炕的硬度,也没有土炕的温度,没住几天,就腰酸背痛,尿频尿急。周末放假后,我骑着自行车,行三四十里路,跑到家里后就一下躺在土炕上了。那种感觉比喝了蜜水还甜哩。只要在土炕上睡一宿,就会感到神气清爽,血脉畅达。
上大学后,可就更苦了我了。因为长年累月住不上土炕,只能在床头贴一张土炕的画像,早晚膜拜,聊以自慰。有个假期,我兴奋地回到老家,突然发现我们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窗明几净,煞是气派。原来父亲在信里说的全是真的。父母高兴地对我说生活好了,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置身于砖瓦房内,我那不由自主的笑声把自己吓一跳。啊,农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美好了。突然,我发现土炕居然也换了造型。什么情况?父亲说那叫吊炕,是用砖块与水泥板搭就的。仔细一看,那炕离地有三十多公分,宛如悬在空中一样。一只小花猫就躲在那炕下注视着我。我以为这炕也是爷爷盘的,父亲说是我伯父盘的。这种吊炕看着确实比过去的土坯炕美观多了,但不知功效如何。当天夜里我失眠了,我在炕上坐起来,发现不远处的那只小花猫也正盯着我看。我们似乎都被对方的眼光吓了一跳。那天的后半夜,我跑到了村里爷爷家的土坯炕上睡着的,舒服极了。
一连好几天,我都在研究“水泥板”与“土坯”间的差异,却没个头绪。父母说不光是我,他们睡这种吊炕也不及过去的土炕解乏。
我结婚前夕,父母干脆把我家的吊炕拆掉了,请来了爷爷还要搭土坯炕。爷爷老了,他是拄着拐杖来我家的,但一到了院子,就一下丢掉了拐杖,瞬间年轻了二十岁一般。母亲也老了,但就是不服老,那干燥规整的土坯都是她一手造就的。这眼前的情形一下就回到了很多年以前的模样。
村里很多的小孩子,如同我当年一样,在新搭的土坯炕上欢快地跳啊、蹦啊。不同的是,孩子们得到的不是那种叫“花生占”的吃食,而是各种各样的甜果和饼干。周围的大人们都乐开了花。
结婚的当天,我和我的新娘幸福地坐在温暖的土炕上,相互诉说无比甜蜜的情话……
小链接尤来顺,常用笔名:尤中文、布里亚特、来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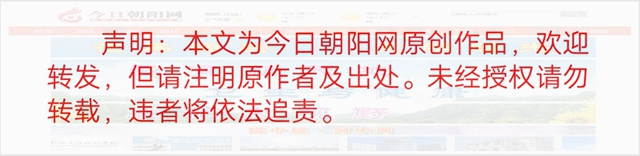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助编 繁花似锦 责编 雅贤]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生日(孙仲兴)
生日(孙仲兴)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初“烤”九天(晏春华)
初“烤”九天(晏春华)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