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
文/文化信使 李法明(辽宁喀左)
小时候十来岁的样子,每到北风渐冷的日子,我就盼着,盼着那个骑着自行车崩爆米花的人,还有那有点嘶哑的声音:崩爆米花来!那个“来”字声音拉得很长,接着就是一阵鸡飞狗跳的,小山村就活了起来。
看到那个盼望已久的老邹头在老王家门前土墙下支上自行车,一群半大小子也不玩撞拐了,那些小丫头也收起毽子,都一股脑儿围上来,胆大的就问问崩一锅多少苞米粒,老邹头习惯地拿出他的搪瓷茶缸,用他特有的声音说:一锅半茶缸苞米,柴火自带。于是哥哥让妹子在土墙下占地方,自己忙着往家里跑,拿早已准备好的硬柴火,倒也忘了天冷了大鼻涕又开始滴答了。
根据经验,第一锅是很少崩得好的,不开花的多,所以大伙就让老邹先崩个响热热锅。老邹也不拒绝,于是往小火堆里加点柴火,一边摇着一边和这帮孩子们闲扯,你是谁家的啊,考试咋样啊。几分钟过后,老邹知道差不多了,把那个崩爆米花的家伙式儿放到一边,一只脚踏上,用勾子一勾,就听见“砰”地一声响,孩子们就知道好戏真的要开始了。
抢了先的孩子很神气,因为可以最先吃到爆米花,看到伙伴们羡慕的眼光也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孩子们都盼着轮到自己,倒是忘了那冻得通红的小手,偶尔用袖子擦一下大鼻涕,袖子就变得更亮了。每当一锅锅飘着苞米香味的大个爆米花新鲜出炉的时候,孩子们就兴奋了,看看谁的米花出得多出得大,当然也会给好兄弟尝尝。那些家里不给崩的孩子就眼巴巴地看着,那眼神真的是望眼欲穿啊,当然也有把老爸老妈缠得烦了挨揍的,那哭得真是悲伤。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拿的都是黄苞米,也有个别的是白苞米,白苞米是自家园子边上种的,都是农家品种,口味很好。白爆米花的品相比黄爆米花好一些,也是值得炫耀的,物以稀为贵嘛。有的孩子还拿点糖精放在里面,爆米花就带着淡淡的甜味,那就是爆米花里的极品了,拿出来倍有面子,只有要好的小伙伴才会分上几个。
小时候家里条件还可以,哪次来崩爆米花的也没让我们失望,有时候就给我们多崩几锅,盛在袋子里,放在不住人的厢房梁上,若放在住人的屋里容易返潮。返潮就不好吃了,当然我们也是拿着方便啊,趁妈妈看不到就抓一把,偷着吃才香呢。
后来崩爆米花的老邹渐渐地就没了踪影,爆米花也成了一种记忆,只是那记忆恍如昨天的故事在心头萦绕,历久弥香。作为渐渐老去的“七零后”,今天在喀左吧里看到了崩爆米花的情景,于是孩时的回忆在脑里蔓延,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回到了那个叫后稠沟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如今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伙伴们,听到了那悠长的吆喝声:崩爆米花来……
小链接李法明,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1975年生人。在辽宁省喀左县五个乡镇辗转打拼二十年,现供职于喀左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喜欢读书,爱好旅游,闲时弄花草,静处赋文章。偶有文字见于报端,愿以文会友,短长互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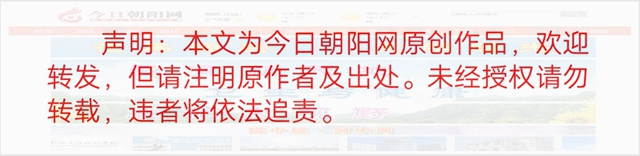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助编 秋水 责编 雅贤]







 怀念凌源小吃(李文静)
怀念凌源小吃(李文静) 闲话饺子(李文静)
闲话饺子(李文静) 天地“粮辛”(孙玲玲)
天地“粮辛”(孙玲玲) 春饼(郭立萍)
春饼(郭立萍) 饺子里的花生米(董军)
饺子里的花生米(董军) 小米情思(李文静)
小米情思(李文静) 美食美客,咀嚼百味人生(晏春华)
美食美客,咀嚼百味人生(晏春华) 十一来啦!安平农场邀您采摘葡萄
十一来啦!安平农场邀您采摘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