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与年轮的故事
文/管丽香(辽宁建平)
四十多年前,在我还是个八九岁孩子的时候,有了一次去往县城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见识外面的世界。只不过,围绕着这次难忘的经历,从头到尾剩下的,就是对一挂马车的记忆。
那个时候,生产队还没解体。一个村庄差不多就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也只有一挂马车。能坐上队里的“公车”出行是件很体面甚至是可以用来炫耀的事。在我仅有的认知中,有关马车的悠久和辉煌,都是活跃在电影和小说里的,能够坐着马车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下,都是上流社会的享受。我只是一个乡下妹子,一定是遇上了好时候。虽然,我搭坐的是一挂拉货进城的马车,但我并没感觉到有多大的差别,我在心里说总之是一挂马车,这就足够了。
这还得感谢我的大哥。当年,大哥二十几岁正是虎虎有生气的年纪。他是一向挑剔的四叔,一手调教出来的“车老板”,那挂马车归他驾驭。
我清晰地记的那个冬天。为了赶路,我在睡梦中被拽出了被窝,鸡正好叫第三遍。天光依稀,一切都在朦胧之中,马车拉着小山似的货物,在沸腾的狗叫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离开了村庄。
马拉的是重车,刚出村子不远,那匹辕马就噗噗地打起了响鼻。马车一直很缓慢地行驶在砂石路上,时不时让乱石块咯得剧烈地晃动起来,好几回我差点像一个包裹一样从顶上滚落下来。一路上,我时刻担心着马车会从沟沿上面翻到深沟里,或者一不小心被其他擦肩而过的马车挤扁,我处在极度恐惧之中,甚至有了一种濒临死亡随时准备好跳车的想法。我自顾自地胡思乱想,竟然没有听到大哥甩着长鞭急促的吆喝声,眼前的陡坡,车子几番较劲都没有爬上去,我被大哥粗暴地喊下车,冻僵的手脚像现按上的假肢,一点都不听使唤。此时,我全然没了进城的兴致,只想尽快结束这趟担惊受怕的旅程。然而,余下的路我怎么管得了,不论再怎么后悔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马车继续往前走,那就是江湖上所说的身不由己吧。
从村子到县城,大约要走六十多里山路,空旷的山野一遍遍回荡着大哥的驭马声和尖利的刹闸声,那些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度盘旋在我的耳边久久挥之不去。历经了六个多小时的颠簸,当太阳从头顶照射下来的时候,我们总算平安抵达了县城。眼前笔直的柏油路,好似一剂良药,让我的身心彻底放松,那一刻我摊倒在马路边上,再也没有精力去关注我梦想中的精彩世界。
此后,我再也没坐过那挂笨重的、令人不安的马车进过城。与其说我淘汰了一挂马车,莫如说我赶上了马车时代的没落。从此,我在心底里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不想再过这种有距离的生活。当然,这种触动,我没向任何人说过,我怕别人笑话我太牵强。实际上,生活本就是这样,看似尘埃一样的小事,或许能改变你的一生。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全面恢复了师范教育招生,我是第一批从初中生考取的师范生。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看到有人接了他的班自然是高兴不已。那天我去体检,老父亲便自告奋勇骑着自行车送我去县城。
这台永久牌自行车,是1979年末父亲平反后给自己买的唯一一件物品。“文革”结束后,父亲顺利地回到了三尺讲台,并补发了工资。他先用这笔钱为两个长大的儿子操办了婚事,然后才用所剩无几的余钱买了这辆自行车,这辆车被父亲誉为不吃草不吃料的“痩驴”,平时并不舍得多用。
三十多年前的公路多是就地取材的黄土路,廉价的砂石路都属于稀有路段。人逢喜事精神爽,将近六十岁的老父亲载着我一路飞奔,很快到了一个叫做官坟梁的地方。那是个倔坡,年轻力壮的单身汉子,也很难一鼓作气爬上去。父亲不服老,载着我吭哧吭哧往上蹬,我强烈要求下车推他几步,父亲回头笑着连连摇头,他害怕累着我体检过不了关。就在我们父女俩拼命上进的时候,车链子经不住俩人沉重的负荷“蹦”的一声断裂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尴尬的父亲只好推着车子和我一路小跑赶往县医院。然而,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怕什么来什么。我们父女俩还是误了体检的最后期限,眼睁睁地看着体检的大夫脱下了白大褂。天下苍生,那辆具有标志性的自行车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八年寒窗苦读,一个农村孩子眼看着错失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却无能为力。我顾不上斯文可着劲地哭,父亲脸色煞白,一遍遍央求着大夫,善良的大夫终于答应请示院长,破格为我做了体检。这个发生在自行车时代的故事,也只有发生在中国,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是最讲究人情的国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出门办事,人们不再依赖单一的绿皮火车和在公路上疾驰的客车,在京城或者大一点的城市,但凡手中有些积蓄的人家开始购买了轿车。我生活的辽西,历史上的“三燕”大地,因其“苦寒”,生活质量自然会差上一截。即便如此,争强好胜的人们从没放弃过追逐的脚步,有些人家凑钱购买了客货两用车,总归是四个轮子的汽车,具备着同时代一样的速度,并不显得怎样落伍。
1986年,我去乡下订婚,和我同去的家人就是坐着这样的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田埂上。彼时,乡村的偏僻和封闭还没有多少人见识过汽车。我们的到来打破了乡村的平静。五六月份,那些在田间忙碌的老人,直起腰板像看稀罕景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微笑着,脸上夹着汗水和泥土的皱褶,像河水一样散开。
等到吃完饭,发动汽车准备返回县城的时候,村里有几个年轻后生,非求着司机师傅拉上他们一程,体验一把坐汽车的感受。农村订婚“说道”多,为此婆婆连哄带骗,硬生生把他们撵下了车。小伙子们丢了面子,涨红着脸发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买上自己的轿车,而且让婆婆们随便坐。巧的是,几年前我在街里还真遇见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岁月如刀,十年的时间早已把当年的毛头小伙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在村里建设蔬菜小区,连年成片扣种大棚,他自己早早地脱了贫,还带动周边的亲戚朋友过上了富裕生活。末了,他极其认真地邀请我坐他的车,回村子去采摘新鲜的蔬菜。这回,该轮到我红了脸,一向以城里人自居,我的生活却落在了他们的后面,看来我得痛下决心努力了。
2014年,我家也如愿买上了轿车,一台高配的黑色“马六”。开到家,停放在车库门口,人们过来过去却熟视无睹,全民轿车时代,家里拥有一辆车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难以表达的激动心情似乎被邻居的“漠视”压抑了,到了夜间夫妻二人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你一句我一句,共同感叹着生活的巨大变迁。朗月清辉,树影贴上了窗帘,不久,屋子里便传出了轻微的鼾声。
自家有了汽车,让出行变得随心所欲。最近六七年,一家人可谓是车轮滚滚,一路风尘。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车为每一个家庭打开了一扇窗,从都市旎祣到乡野风光,原本落后的村庄,因为“原生态”一夜蹿红,成为吸引大批旅游爱好者光顾的地方,一方经济藉此红火。某种程度上说,汽车进入家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催生了“车轮经济”。
今天,我国迎来了全面高铁时代,银蛇蜿蜒,高铁站修到了家门口。一日千里,曾经的神话变成了现实。2021年1月20日,在冰天雪地的辽西,途经我的家乡开往北京的高铁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疾驰而去,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原来绿皮火车8个多小时的车程缩短不到2个小时,古老的朝阳真正成为了首都的后花园。朝阳搭上了富亲戚,好日子还会远吗?
高铁终结了长途旅客饱受的舟车劳顿之苦。对于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旅者,家庭轿车失去了许多用武之地,已是昨日黄花。在世界速度面前,没有谁能够阻挡住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光阴似箭,车轮接力,百年中国恰似风华正茂。我看到,广阔的大地坦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母亲召唤着儿女,大地召唤着未来……
小链接管丽香,汉族,1966年出生,辽宁省建平县人。辽宁省作协会员、朝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建平县原文联主席。先后在《海燕》《辽河》《芒种》《中国绿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随笔80余篇,主持编辑出版了《清代喀喇沁右翼蒙古王陵石雕艺术》《建平民间艺术》《建平文艺群英谱》等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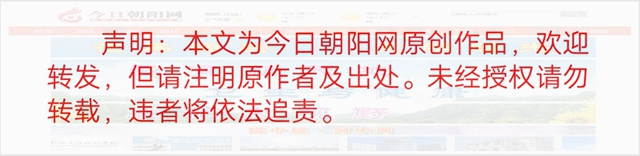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生日(孙仲兴)
生日(孙仲兴)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初“烤”九天(晏春华)
初“烤”九天(晏春华)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