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娘为我戴花
文图/刘贵成(辽宁朝阳)
2004年6月16日,是一个让我发自灵魂深处大喜大乐,且略含无奈与悲戚的日子。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足令我的后半生在一丝幸福和平淡无奇的喜悦中,悄悄生长出一种久违的欣慰。
上午,与妻一起搭朋友的车回老家。为父母亲建的新房落成一月有余,两位老人早已匆匆入住。建房的活全包出去了,按理说没有多少令人操心的事。但是,房子上盖的当天,就忙着以灰捶顶,两天后,便有消息传来,说房子没捶好,裂了许多蚂蚱口。担念房子漏雨、地面处理、墙是否还湿、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状态等等,心急火燎般往回赶。
车到村口,见一帮乡亲在树荫下闲坐,远远就打招呼,每个人的脸上都漾着一层笑意。一抬眼,不经意间看见一幅图画:新建成的砖房旁边,一大丛高过人头的刺梅菊花繁影俏、粉色盈盈。花旁的土井伸出一根长长的塑料管子,一端探向北方。一位白发蓬乱、身材矮小、衣满褶皱然而却头上戴着一朵粉花儿的老妇人,双手握着水管,将一条白色水柱扬向一小片葱地。另一位身材高大、背略微驼、脸黑发白、声若洪钟的老年男性,站在电闸旁,似在指挥老妇人浇葱。只在一瞬间,感觉初夏的阳光,正均匀地撒播进那幅田园画中。新落成的房子益显高高大大,红砖、白窗、粉花、绿葱、黄土,各种色彩交织、重叠,满眼的新鲜感觉。喷涌的水柱、摇曳的花影、走动的老人、鼓荡的热风,使这幅画突然活了起来——这就是我的家、我的父母。
父亲最先看见我们,布满褶皱的长瓜脸上流泻着孩子般的笑。母亲正背对着我们,一心浇着那几垄葱。细看看,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水在葱垄中间早已积水成潭,但靠北部约一米长的垄沟里却滴水未落。“你老小子回来了!”父亲对着疯娘大喊一声。母亲缓缓地转过头来,和我的目光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下对接,没发一声,“啪”一下扔掉水管,径自向井旁的花丛走去。和乡亲们寒暄、拉话的时候,母亲踮起脚尖,从花枝的高处,轻轻摘下一朵粉色小花来,脸上竟挂着几许怪怪的笑意,好象还在自语什么。
进到屋里,我忙着查看施工质量,没有注意疯娘在干什么。里里外外看完一遍,也许有十多分钟,待我走进里屋时,猛一抬眼,看到疯娘左手拿着一朵粉花,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依然怪笑着,只不过比方才的怪笑更猛烈,简直有点恶作剧的意味。但就在我再进一步时,恍惚中见到疯娘一向浑浊、木然的双眼里,正发出几丝,不!是几缕慈爱的微光。不知为什么,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我的心莫名地抽搐了一下,随即有一股温温的暖流涌向心头。要知道,自从生我坐月子就患上精神病的母亲,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准确点说是从我记事后,从娘的眼里就一直很少读到母爱的慈光。娘的病从轻到重、从间歇性发作到常年癫狂,打东邻、骂西居、砸家什、频出走,记忆中悲情凄苦的小家,很少听到笑声。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因赶大车砸断了右腿,年逾古稀的祖母被迫到姑母家居住,几乎失去父母疼爱的我们三兄妹,是在乡亲邻里的同情与关照中长大的。母亲柔和而慈祥的目光,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奢望。
我真的没想到,此刻,手里拿着小花的母亲,竟在这么多年以后,用独属于她的、并不十分真切的慈爱目光来看我。或许就在几秒钟之间,与我对视的疯娘,目光变得更清亮起来,同时伸出右手来抓我的头发,一边笑着说:“老小子,戴朵花吧”。我在惊异中本能地躲了一下,顺口说道“小子哪有戴花的?”但没想到的是,疯娘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停手,她向我迈进一大步,踮起脚尖,左手高举小花,右手仍在努力地够我的头发,布满褶皱的脸向上仰着,嘴里还在叨念“戴上吧,戴上吧”,一副小孩子相。站在一旁的父亲笑着说:“打搬进新房子那天起,你妈就傻乐,净出洋相。”这时,躲闪中的我将小花碰落,母亲弯腰拾起,仍旧笑闹着坚持给我戴,呼吸声明显有些急促,满头白发在狂舞,一股汗味儿在飘散,我的鼻子突然狠狠地酸了一下,说不清的感觉让我骤然麻木起来。这时,妻子说话了:“妈让你戴你就戴吧,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哄妈乐不就得了吗。”我猛然理解了妻子的用意,顺从地低下头来,任由母亲给我戴花。可能是花朵太小,加上我的头发太短,花再次掉落。母亲说:“等一会儿,我找线去。”当我缓过神来环视四周时,见到妻子正娇笑着,手里拿着数码相机对着我们。母亲找来一条白线,对折一下,用双线来为我“绑”花,大约用了五六分钟才大功告成。刚刚腾出手来的母亲终于发现在一旁拍照的妻子,竟再一次发起孩子疯来——对着镜头做了一个鬼脸,随后在开心的笑声中和我认真合影。不知什么时候,我的两行热泪早已如瀑飞下,咽喉处直觉堵得慌。我知道,已近不惑、身材魁梧的我,不可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纵情地投入母亲的怀里撒娇,应该属于我的那一份童年幸福早已随风散去。也许是怀着一种委屈,抑或是一种久违的激情与冲动,我用手紧紧抓捏母亲的右肩,双眼一片模糊……
感谢妻子,用相机及时记录下这一特殊的时刻。归来的路上,我一遍遍地回忆着疯娘为我戴花的每一个细节,一边忆想陈年旧事,渐渐地,竟然萌生一种异常的感觉——忧伤、欣慰、满足、自豪、幸福并存。试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位男子,在年近不惑的时候,能够得到如此奇特、如此厚重、如此强烈的母爱?我真切地感悟到,尽管这份母爱来得太迟了一些,但是,当那一朵鲜艳芬芳的小花,牢牢地绑在我的头上时,我还是很知足。阳光照耀下的一草一木、目力所及的群山白云,尽显祥和妩媚。
稍稍冷静下来,追寻这份幸福的根源,除真诚感谢妻子外,必须向给我温暖和关爱的乡亲、师长、朋友、同事、领导表示感谢,必须向给我奋斗机遇、提供创业条件的这个社会,以及充满变革和活力的伟大时代表示由衷的敬意!
谨以此文献给天下的母亲
(本文作于200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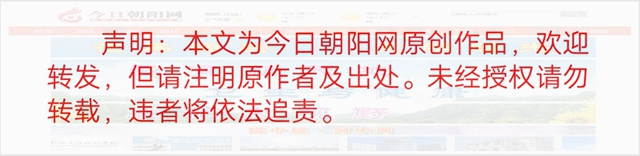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我和书的故事(陈雷)
我和书的故事(陈雷) 人间烟火暖(辛秀玲)
人间烟火暖(辛秀玲) 映日荷花别样红(张俊清)
映日荷花别样红(张俊清) 用心打理自己的日子(周显梅)
用心打理自己的日子(周显梅) 对的选择(周显梅)
对的选择(周显梅) 可爱的小狗(张立芳)
可爱的小狗(张立芳) 又见九月菊(马镛)
又见九月菊(马镛) 乡情(辛春艳)
乡情(辛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