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婶住在乡下
文/管丽香(辽宁建平)
最近几年,有关老家的事我多是听说来的。人上了点年纪,脚下牵绊多,想去的地方总是拔不动步。我听说,老家的五婶已经卧床一年多了,在祝贺老叔八十岁生日的寿宴上,对着满桌的美酒佳肴,我再也没有心情吃下去。
粗算起来,五婶已经八十五、六,他们那一辈至今还留在乡下的就剩她一个了,她的生命力还真是强大。家里儿女没有好事儿的,大事小情想不起来张罗,她就那样一年四季安安静静地呆在院子里。忙时拔拔园子里挤挤挨挨的赖草,给满地找食的鸡呀鹅的撒点谷子、苞米,扔几棵野菜,累了就坐在墙根板凳上晒晒太阳,等攒够了力气她就大声吆喝吆喝那只看家狗,大黑狗势力,摇着尾巴像什么也没听见,这样的光景约摸过了两三年,后来不小心摔了一跤再也没下来炕,从此五婶好像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样。
我想过,五婶也是被忙忙碌碌遗忘的一部分。其实,世间事值得忙的并不多,恰恰是那些不值得忙的事把人们忙得晕头转向。我也成了一个没办法抽身的人。世上的事忙得完吗?我一边自言自语责备着自己,一边动手做着回乡下看望五婶的准备。我心急如焚,竟像年轻时一样冲动毛躁,好像多拖延一天都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五婶是四十出头才来我们村上的,她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妹。和五叔成亲那天,她打扮得非常漂亮,一点都不土气,眉清目秀的,说话慢声细语,走起路来稳稳当当,倒像个从大户人家嫁过来的女人。
五婶是我堂兄妹的继母。五叔娶她的时候,已有一屋子孩子,大大小小六七个站满了一地,他们衣着邋遢吸溜着鼻涕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炕上新亲坐桌的糕点,怎么撵都撵不走。那时,我就夹在他们中间,企图浑水摸鱼,贫穷岁月,糕点的诱惑力,哪是一个十多岁孩子能够抗拒了的。五婶真是聪明人,她似乎早已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其实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得明白,只是更多的人装糊涂罢了。五婶披着大红棉袄,起身,很卖力地抓了一大把沾满白糖的江米条,客客气气地分到我们每个人手里。这时站在她一旁的大姑奶奶,踮着小脚干咳两声,又急忙把她按回到一床绿色被子上坐下,佯装生气地训斥说,别坏了祖宗规矩,新娘坐福不能乱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一直记得那一幕。
五叔在县城一个几千人的国营企业当食堂管理员,听人说,五叔干的是有油水的差事。五叔靠着自己的力量熬到这个位置不容易,他办起事来总是谨小慎微。相隔十天半个月的,五婶家也只能吃上一小盘红烧肉。说是一小盘,实际上就是十块八块的,孩子多瓜分不过来,平日里不受待见的,也只有伸长脖子咽口水的份。
有事没事我最爱去五婶家串门,撞运气的机会自然比别人多。那天我在家里草草地扒了口剩饭,就顶着正午的日头上山去捡蘑菇,三拐两拐还是不自觉地走进了五婶家院子,我去喊堂姐搭伴。临近窗根,就听见屋里热热闹闹地正在你一块我一块地分吃着红烧肉,我悄悄地退回到大柳树下再没敢出声。一个早早就没有了母亲的孩子,强烈的自卑驱使着我越来越自尊,从小到大,我从没因为多贪一口吃食而失去过体面。
五婶还是听见了动静。她热情地拽我进屋还把我抱上炕角,像是早就预留好了,她回避着周围虎视眈眈的眼神,端着一整碗盖着红烧肉的大米饭硬生生地塞到我手里,并一个劲地催我快吃,我眼泪就吧嗒吧嗒地掉进了碗里,那副难看的吃相,那顿饭的味道就永久地凝固在了我的心里。
五婶是党员,又有文化,不久她就担任了大队会计。在她担任会计的第二年,她“以权谋私”,巧妙地帮我躲过了一场劫难,我才得以顺利地读完小学,考上了师范,吃上了“皇粮”。现在,我常常想,如果我的命中没有五婶,或许,和大多数农村女孩子一样,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生子、侍弄庄稼——穹庐之下,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一个女人抡圆了镐头,一镐刨下去,再一镐下去,连续的重体力消耗几乎让她没办法站稳脚跟,她拄着镐头拽过衣襟擦着满脸的汗水,这应该就是属于我的乏味而雷同的日子吧……
那年我刚满十三岁,就被父亲分派到离家最近的一块谷子地拔苗子。那块地环绕在一座小松树山的山根下,肥沃的黑土散发着淡淡的松香,一脚踩上去就像踩到刚出锅的馒头一样喧腾,这是村里最好的土地,更是一块被家里人寄予厚望的土地。记得当年,遇见了少有的风调雨顺,地里的青苗长得又粗又壮,像覆盖上一层绿色的绸缎,风刮过后是一道道长长的波纹。
我们兴奋地蹲在垄背上,按照以往拔苞米苗子的经验仔细地分辨着高矮,留下最高最壮实的苗。天知道,就在我们汗水淋漓希冀着好收成的时候,一块能够生长金黄色小米饭的土地却被轻易地毁掉了。我们良莠不分,薅掉了正宗的谷苗子,留下的是结不了谷穗的莠子,一地鸡毛,我们家成了全村人的笑话。父亲暴怒之下,竟然喝令我们退学回家,理由很充分,连庄稼都侍弄不了,上学能有出息?我没做任何分辩,为自己的无知和自负惭愧不已。
热在三伏,更何况已近晌午。我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泥水,急忙找块石头垫在屁股底下,把筐里的野菜全部倒在地上认真地挑选起来。家里的口粮不多了,等着掺和野菜贴饼子下锅,我也是尽量做好每件事,好让本以愧疚的心得到些宽慰。这个时候,五婶急匆匆地进了院子,她只和我摆了下手便径直进了屋。屋子低矮,为消掉暑气,整扇窗户都敞开着,五婶和父亲的对话一句不落地被我听下来:
“二哥,我帮你申请了困难补助,150斤白苞米,你看解点劲吧?”
“定准吗?你费心了!”
“二哥,听说你家横沟子那块地撂荒了,有这150斤苞米顶着也差不太多,你就让孩子们回学校吧,给我个薄面!”
“二哥,你是个有眼光的人,孩子的前程不能耽误,家里的活计忙不过来我抽空过来帮帮行吗?”话音拖着哭腔。
父亲沉默了半晌,我的心咚咚直响几乎要跳出胸膛。还是五婶先打破了沉寂,她说:“我把孩子领走了,老师在门口等着呢!”
转年的春天,野菜刚刚长出地面,青黄不接那是农村最艰难的季节。孩子们放学后扔下书包就往大地跑,漫山遍野都是一个个快速移动的小黑点。五婶家的人最多,几乎是全员出动。堂姐和往常不一样,一路紧跟着我,浑身上下鼓荡着一股怒气,总是和我抢个不停,甚至故意把菜铲碎了散落在地上,我终于忍不住夺下她的筐子扔出了老远——背后是她嘤嘤的哭声,她还让我还她家的苞米?
原来,是五婶把她家里的苞米给了我们,那一年大队压根就没有困难补助一说,好似石崩天裂,我咬紧嘴唇仿佛天上的白云都跟着我一起旋转,那年月粮食好比黄金珍贵,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40多年后,在一个深秋的下午,阳光碎金子一样洒在大柳树的叶子上。那棵大柳树长在五婶家大门口已有上百年,高耸的树冠盖过了村子所有的大树,它成了一个村子的标志。此刻,我拥抱着风烛残年的五婶,早已是泪流满面,而她却端详了半天也没能叫出我的名字,她认得我,只不过是她不敢相信,我会百里之外特意赶回去看望她。“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岁月残酷,病榻上的五婶顶着稀疏的白发,两眼嵌进深深的眼眶,两腮沟壑纵横塌陷进没有多少牙齿的嘴巴里,“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她垂老的样子已经没有多少年轻时的影子。
然而,五婶却一点都不糊涂,即使半闭着双眼也能判断出园子里各种鸟的叫声。她认认真真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一定在家里多住些日子,你下次再来说不定就看不着我了。我心里酸酸的,脸上却堆着笑干脆地应答着,我原本就有这个打算,我是要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她老人家的。
在这个果实累累的季节深处,坐在轮椅上的五婶迎着斜射下来的万道霞光,像极了菩萨的尊身。
小链接管丽香,汉族,1966年出生,辽宁省建平县人。辽宁省作协会员、朝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建平县原文联主席。先后在《海燕》《辽河》《芒种》《中国绿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随笔80余篇,主持编辑出版了《清代喀喇沁右翼蒙古王陵石雕艺术》《建平民间艺术》《建平文艺群英谱》等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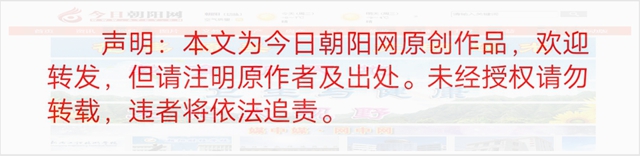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生日(孙仲兴)
生日(孙仲兴)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初“烤”九天(晏春华)
初“烤”九天(晏春华)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