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枝沙棘凌寒开
文/文化信使 沈德红(辽宁朝阳)
当漫天风沙裹着枯枝败叶在山野打滚时,没有了鸟鸣,没有了潺潺流水声,整个村庄似乎也要进入冬眠状态。可村庄里的人知道,在小村东头那条河岸边,一大片沙棘果正在擦胭抹粉,准备闪亮登场。
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大部分农村的沟边都生长着沙棘。这种从千百年前就在乡村落户的纯天然植物,陪伴着村民走过了无数个日子。无论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的岁月,沙棘树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守护着河流,拥抱着小村,给饥饿的村民果腹,从未离开过。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牵着我的手,挎着的小筐里,放着一把镰刀,去那片沙棘林摘沙棘果。
穿着妈妈为我做的棉袄棉裤,戴着姑姑为我缝制的狗皮帽子,妈妈又给我围上她的红围巾,我只露一双眼睛在外面。我好奇地巡视着,沙棘树一棵挨着一棵,上面的果实有红色的,有黄色的,一串串的,像珍珠,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是那样的唯美,打动心扉。
禁不住沙棘果的诱惑,我会蹒跚着脚步,去摘压弯枝的沙棘果,扯下头巾,塞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口齿留香。
妈妈总是惊呼着阻拦我,她怕那树杈上的刺扎伤了我。因为沙棘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刺,所以当地村民都习惯叫沙棘为刺柳。
妈妈嫌摘沙棘果太慢,手不小心会被刺伤流血,就用镰刀割下来几枝,去封冻的河面上摔打果实。来回折腾几次,才摘满一筐,再在树上折下来果实密集的一枝给我拿在手里,领我回去。村里采摘沙棘果的人很多,大家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有说有笑的。妈妈是教师,大家见了她都打招呼,还顺便掐一下我的脸蛋儿。
这些果实拿回家后,妈妈把它们储藏在一个罐子里,拌上少许白糖,用小勺分给我们兄妹三人吃,那又甜又香的味道,我至今难以忘怀。
城里的亲友,每次来家里做客,走时妈妈都会给他们带上一罐头瓶沙棘果,有一年,一个奶奶病了,妈妈把沙棘果几乎全给了她。我才知道,沙棘果还是药材,能治疗一些疾病。
我长到七八岁时,再也不愿意随妈妈去摘沙棘果,而是约了几个同龄的女孩子一起去。
内蒙古的冬天嘎嘎冷,小风像刀子割我们的脸和手。我们像勇敢的小战士,在寒风中摘沙棘果。我们认为,在万物萧条的冬天,摘沙棘果是最开心的事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沙棘果是多么好吃的东西呀!我们这些小馋猫,哪管冰天雪地,再冷也要去。
上学以后,每次摘沙棘果时,我都会给伙伴们讲妈妈给我讲的故事。我说沙棘果在千百年前就有了,说成吉思汗远征赤峰时,人困马乏,饥饿难耐,许多士兵得了重病,多亏遇到一片沙棘树,人吃沙棘果,马吃树叶后,士兵的病好了,战马有了力气,打了一个大胜仗。伙伴们停止了打闹,听得入了迷。
在我的姑娘时代,这片沙棘树的领地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冬天的色调单一,荒凉让人心生浮躁。走近沙棘果,那晶莹剔透的果实,那火一样的红,会点燃你心中的希望。
当岁月的脚步,把我追到了婚嫁年纪,我远嫁他乡。我出嫁的那天,天降祥瑞,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像玛瑙一样的沙棘果上,那白里透红的精致,美丽,让我瞬间热泪盈眶。我无法割舍我对沙棘果的留恋和不舍。那天的画面,永久地刻在我的心上。
我远嫁到辽宁,婆家的小山村里没有沙棘树。
听故乡的亲友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棘果因为有止咳化痰、活血化瘀等功效,被大量采购,做成保健品销售。多少年固守乡村的沙棘果,走出了这片土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身在异乡的我,因为娘家搬迁城里,细数光阴,我整整二十多年没有回去了。每次在商场看见由沙棘果制作的饮料和食品,都买回家,仔细咀嚼乡愁,回味沙棘果昔日的清香。
瞬间,记忆就像长了翅膀,脑海里如电影镜头一样回放,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沙棘果亲密相处的片段以及思念、乡愁潮水般涌来,泪水瞬间迷蒙了双眼。
透过时光的隧道,我仿佛回到那远方的故乡。
我依旧挎着小筐,和几个小女孩说着笑着摘花一样美丽的沙棘果,我们的脸蛋和沙棘果都被阳光晒得红扑扑的……
(本文发表在《辽宁青年》,经作者授权编发,编发时略有改动)
小链接沈德红,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朝阳作家协会会员,北票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新西兰华文报》等多家报刊及今日朝阳网等网络媒体。有作品入选《启功文化在赤峰》《青年作家年鉴》《在希望的田野上》选本,作品多次获奖,接受过媒体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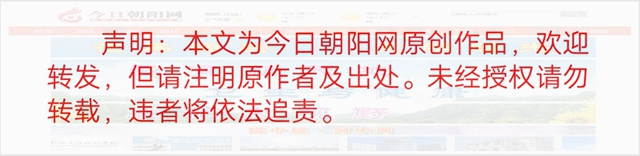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生日(孙仲兴)
生日(孙仲兴)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初“烤”九天(晏春华)
初“烤”九天(晏春华)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