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地界:圪塔〔gā da〕
文图/文化信使 吴歌(辽宁锦州)
“……应有尽有,这嘎达生意太火啦!”——东北新闻网(20141014)《首届中国东北商品交易会:这嘎达生意太火啦》。
“还跳栏杆,这嘎嗒都撞死多少人了”。——环球网(20160314)《吉林一天桥挂条幅劝横穿行人:地狱无门你翻栏杆》。
“你们哪旮嗒的?”——新浪(20040520 转自哈尔滨日报)《记者探访近郊小钢厂》。
以上三例中的“嘎达”“嘎嗒”和“旮嗒”,按照当下东北方言主流辞书里的“标准答案”,似乎都应该写成与之同音的“疙瘩”。媒体记者们,不会不知道吧?之所以“明知故犯”,或因为忌讳“疙瘩”之“疒”。
“把昨天剩的几疙瘩肉切切炖上!”——董联声编著《中国·东北方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5年)中“疙瘩”之例句。
“一疙儿茶肠”;“一小疙儿咸菜”。——尹世超主编《东北方言概念词典》(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中“疙儿”之例句。
用于食物的量词“疙瘩”或“疙儿”,写在纸上,既已带“疒”;看在眼里,谁不扢膺〔gè ying〕?
拙作《东北方言注疏》认为,“疙瘩”与“圪塔”,音同形似义别,并非异形词。“疳”与“坩”,可为镜鉴。语义无关“肿块”者,应作“圪塔”;语义关乎“肿块”者,应作“疙瘩”。
“疙瘩”与“圪塔”哪一个符合规范?其实它们的基本词义相同,只不过是用在不同的场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根据社会通用性的大小和约定俗成的原则,以社会通用的语言事实为根据,明确引导大家使用“疙瘩”。——新浪(20031118 转自汉网)《“空穴来风”是何意?“疙瘩”“圪塔”该用谁?》。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依据的“社会通用性”和“约定俗成”原则,在此可能无法相提并论。因为“疙瘩”与“圪塔”同音,口语层面的“gā da”,形成文字时,在前者与后者之间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写字者,而非说话者。
诚如谭慧敏/左飚《词汇语义与社会文化——“同志”的词义演变所引发的思考》(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7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年)所说,“语言对社会上所有的使用者都是平等对待或一视同仁的,但使用者却在‘不平等’地使用语言,这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语义的选择和理解上……。”
空口无凭,立字为据。这句俗话,可谓上文所说“不平等”的现实写照。口头的语音,纸面的文字,在语义的选择和理解上可能没有干系,甚至背道而驰。
“圪塔头是要家庄乡的一个行政村,地处桑干河北岸,与揣骨疃镇曲长城村隔河相望。”——张家口悦读《阳原古村落“碰了疙瘩”的圪塔头村》(微信 20201110)。文章说,据《阳原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该村建于明初”。村名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村子最早居民住在村子附近的土圪塔上得名;另一种说法是过去天上掉下一块陨石,该村与邻村牛蹄庄争抢未成,所谓“碰了疙瘩”,故名疙瘩头,后改称圪塔头。
“疙瘩”头,改称“圪塔”头,堪称语音凭借“社会通用性”取胜的具有标本意义的案例。
曹静《词义的社会性》(逻辑与语言学习 1984年03期)指出:“词义不是人们的臆造,而是来源于客观现实,因为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文章说,词义中所包括的内容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社会的习惯,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这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
曹静先生文中“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的“约定俗成”,显然不是写字者们的“约定俗成”,而应该是说话者们的“约定俗成”。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据查,在亿万华夏儿女心中故乡的洪洞县,几百个村子的名称用字,难以见到“疙瘩”以及“疙”,却能见到“圪塔”以及“圪”。临近的陕北米脂和绥德两县,亦如是。个中原因,是否在避讳“疙瘩”之“疒”呢?
常言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然而,熬(煎)药用的瓦罐,因为与疾病同行,例外地不需要“诚实守信”。用后归还借来的药罐子,系民俗中的禁忌项。
趋吉避凶,儒者之事。仅仅依据理论上的通用性,取“疙瘩”而舍“圪塔”,令居住或行走都要置身于带“疒”的“疙瘩”之中,情何以堪?
小链接吴歌,曾用名吴戈。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高级经济师。锦州市“最佳写书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锦州方言”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语言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摄影协会会员。金融专业论文和业余摄影作品,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奖。散文《丁香雨》入选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赛努呼和浩特系列文集·散文集》。出版专著《东北方言注疏》(白山出版社 2016年)。参加编著《人文锦州·民俗风情卷·锦州方言》(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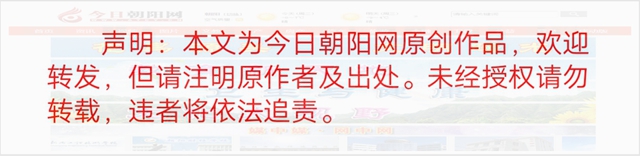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春节不是年(吴歌)
春节不是年(吴歌) 【今日朝阳网】怠〔dāi〕之新证(吴歌)
【今日朝阳网】怠〔dāi〕之新证(吴歌) 爷娘与尊卑(吴歌)
爷娘与尊卑(吴歌) “憋亮子”异说(吴歌)
“憋亮子”异说(吴歌) “亮子”两说(吴歌)
“亮子”两说(吴歌) 傻姑爷子吃鸡(吴歌)
傻姑爷子吃鸡(吴歌) 【今日朝阳网】奇葩娱乐:咬姑娘儿(吴歌)
【今日朝阳网】奇葩娱乐:咬姑娘儿(吴歌) 儿化也有不归路(吴歌)
儿化也有不归路(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