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化也有不归路
文图/文化信使 吴歌(辽宁锦州)
王中原先生《慎用儿化音》,系王中原绕口令第470则,见于今日朝阳网(20210308)《王中原绕口令〈李频和吕芃〉外一则》。
儿化音用于诗歌韵脚,饶有趣味儿。
广为传唱的东北民歌《串门儿》和二人转唱段《双回门儿》等,可谓用儿化音作韵脚的典型。
我活着是你的“人”儿,死了是你的“鬼”儿。流行歌曲《依兰爱情故事》这两句词,利用儿化音令“人”“鬼”同韵,别有洞天。
既然饶有趣味儿,为什么还要“慎用”呢?王中原先生《慎用儿化音》这么说:“牛贵”儿化成“牛贵儿”,听起来像“牛棍儿”;“刘卉”儿化成“刘卉儿”,听起来像“刘混儿”。
不慎使用的儿化音,会有怎样的弊端呢?王先生《慎用儿化音》这么说:本来“刘卉”“牛贵”成双对儿,误传为“刘混儿”嫁“牛棍儿”。
“刘卉”与“牛贵”,误传为“刘混”与“牛棍”,问题出在哪儿呢?
拙作《东北方言注疏》称这类现象为“去儿化误导”,属于“儿化的功用”的负面效应。
林焘 沈炯《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 1995年03期)指出,北京话儿化韵中有一些韵母存在着明显的个人语音分歧。如:(刀)把儿=(花)瓣儿;(肩)膀儿=(木)板儿。这就意味着,音节“bar=banr=bangr”。
张俊英《后鼻音儿化韵发音偏差种种》(教学与管理 2005年18期)指出,在方言的影响下,前后鼻音的儿化韵字变成同音字。如:好样儿=好燕儿;小风儿=小分儿。这就意味着,音节“yangr=yanr”;“fengr=fenr”。
不论是“语音分歧”还是“发音偏差”,现象背后的实情都是令儿化的“化学反应”难以“还原”——所写难以符合所说。东北人和北京人笔下的“张巴样儿”,到天津人笔下变成“张巴燕儿”,堪称“好样儿=好燕儿”的活标本。
类似“卉>混”“贵>棍”“样>燕”的“去儿化误导”,经过教科书式的“xiàngr>xiànr>xiàr”的儿化之后,再逆向“去儿化”时,“xiàng”讹变为“xiàn”或“xià”存在客观上的可能性。同理,“xià”讹变为“xiàn”或“xiàng”,也存在客观上的可能性。
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和北京土音的界限》(全国普通话培训测试信息资源网 20130407)认为,八下里(各方面)之“下”,语音为“xiàn”,系“xià-xiàn”的“增韵尾”之变。
空间的向度,不外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向度(方向/方面)都为“下”,似乎比较难。八向儿、四向儿与两向儿,长向儿、宽向儿和高向儿,或夸张,或如实,焉能无不为“下”?
说“xiànr”写“下”,概因“去儿化误导”使然。具体地说,因为“xiàngr=xiànr=xiàr”,去掉儿化韵尾“r”之后,所得“xiàng=xiàn=xià”便成为语音上的罗生门,令人难以定夺。
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到山顶重逢。福楼拜的这句话,可否这样理解:科学需要追求艺术的美丽,艺术需要尊崇科学的真实。
再看语音为“xiànr”语义为“向度”的“向儿”。即使在一维空间里,两个向度也不可能都叫“下”,遑论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说“向儿”写“下”,实质上跟说“卉儿”写“混”和说“贵儿”写“棍”一样,均为“去儿化误导”令本字走上的不归路。
当然,越是贴近日常生活用语的儿化音,越不容易受到“去儿化误导”,越不容易令本字走上不归路。假设听到喊“冰棍儿”,相信很少有人会写成“冰柜”。倘若写成“冰柜”,所谓的“约定俗成”恐怕也难以为其背锅。
小链接吴歌,曾用名吴戈。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高级经济师。锦州市“最佳写书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锦州方言”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语言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摄影协会会员。金融专业论文和业余摄影作品,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奖。散文《丁香雨》入选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赛努呼和浩特系列文集·散文集》。出版专著《东北方言注疏》(白山出版社 2016年)。参加编著《人文锦州·民俗风情卷·锦州方言》(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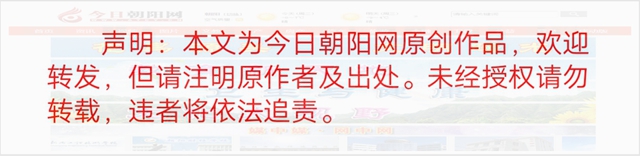
[编辑 立军]












 春节不是年(吴歌)
春节不是年(吴歌) 【今日朝阳网】怠〔dāi〕之新证(吴歌)
【今日朝阳网】怠〔dāi〕之新证(吴歌) 爷娘与尊卑(吴歌)
爷娘与尊卑(吴歌) “憋亮子”异说(吴歌)
“憋亮子”异说(吴歌) “亮子”两说(吴歌)
“亮子”两说(吴歌) 傻姑爷子吃鸡(吴歌)
傻姑爷子吃鸡(吴歌) 【今日朝阳网】奇葩娱乐:咬姑娘儿(吴歌)
【今日朝阳网】奇葩娱乐:咬姑娘儿(吴歌) 儿化也有不归路(吴歌)
儿化也有不归路(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