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娱乐:咬姑娘儿
文图/文化信使 吴歌(辽宁锦州)
揪姑娘儿,透姑娘儿,
小丫丫儿一起咬姑娘儿。
小嘴噘,舌尖裹(啯),
看谁咬得好听咬得响。
这段歌词,见于明明简谱网(20191120)《咬姑娘儿》。“咬姑娘儿”所“咬”的“姑娘儿”,系野果名,学名酸浆。此处之“娘”,要说成“niǎng”,还要儿化。姑娘〔niang〕,指人;姑娘儿〔niǎngr〕,名物。用声调来区别语义,可谓中华语言的智慧。
作为植物及其果实的姑娘儿,大致有两种:红姑娘儿和黄姑娘儿。红姑娘儿个儿稍大,味苦,也叫苦姑娘儿;黄姑娘儿个儿稍小,味甜,也叫洋菇娘儿。
查阅《康熙字典》可见,红姑娘儿较早见于徐一夔《元故宫记》。
清代纳兰性德写过一首词,题为《眼儿媚•咏红姑娘》:
骚屑西风弄晚寒,翠袖倚阑干。
霞绡裹处,樱唇微绽,靺鞨红殷。
故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
玉墀争采,玉钗争插,至正年间。
燕京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甘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本草纲目》解读“酸浆”的这段话,因包括“绛囊”和“赤子如珠”,如今有学者将其推测为《红楼梦》里绛珠草的原型。
《本草纲目》对“姑娘”二字存有疑议。指出,姑娘乃瓜囊之讹,古者瓜姑同音,娘囊之音亦相近耳。瓜囊,语音姑且不论,形象是否过于夸张?
时下,也不乏对“姑娘”二字存有疑议者。
“菇娘,这个‘娘’字应该是带草字头的,但是字库里没有这个字,就用‘娘’字替代了,读音作niǎng。”——莉莉(lily)《咬菇娘》(新浪博客 20080819)。博主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姑鸟儿”,见于尹世超主编《东北方言概念词典》。其“鸟”,或为规避“娘”字的变通之举。
拙作《东北方言注疏》认为,姑娘儿〔niǎnger〕,应为姑娘〔niang〕果之懒音(减省)。之所以称其为“姑娘果”,是因为“咬姑娘儿”系姑娘们的专属娱乐。
作家郑旭东乡情散文《菇娘儿》写道:小女孩“咬菇娘”非常有趣,她们从高粱秸秆扎的笤帚上,折下一根像牙签一般的细小枝杈,在菇娘儿果芥蒂(结蒂)处扎一个细微的小孔,将里面甜蜜的汁水和细小的种子吸允(吮)干净,然后放入口中用舌尖轻轻地反复揉搓。很快,菇娘儿果皮就会变得柔软许多,犹如一个微小的气球。在口舌的作用下,已变得空荡柔软的菇娘儿果皮被齿舌凭着微妙感觉找正方向,并且固定在齿根和舌尖位置,顺次完成吹气(吸气)过程促其鼓胀(令其充满)……在腮齿作用下完成一套轻柔的挤压。于是,“咕咕,咕咕”一串串清晰有趣儿的声响就接连不断地响亮地传出来,那种特定的响亮和惬意感觉,甚至比现在的孩子吹泡泡糖还有趣儿。
当代作家李百合《“毛毛道”上的流年》写道:这个季节,不论是在碱沟里,还是在房前屋后的树趟子里、大田里或柳条地里,都生长着红菇娘儿和黄菇娘儿。红菇娘儿要等到熟透吃,但味道不好;熟透的黄菇娘儿非常甜,味道好极了。那时候的毛道两旁或两旁的庄稼地、沟边子或树林子里,都有上一年随意“柳生”(稆生/穞生)下来的野菇娘儿秧,很大的一“趴拉”(趴落)一“趴拉”地生长着。菇娘儿不但能食用,而且还是一种玩具。把菇娘摘下后,用笤帚糜子(篾子)的小细枝把其尾部扎出一个眼儿,把里面的籽液挤出,吹鼓,含在嘴里能咬出响儿来。女生就爱这种游戏……含在嘴里自然熟练地就能把菇娘儿皮吹大,而后咬响。
《咬姑娘儿》中的“小丫丫儿”,乡情散文《菇娘儿》中的“小女孩”,李百合《“毛毛道”上的流年》中的“女生”,都在姑娘〔niang〕年龄段内。
唐朝以前,爹娘之娘另有其字,即“孃”。娘,乃少女之号,即姑娘〔niang〕之“娘”。
咬姑娘儿的娱乐,以及由此派生的姑娘果的别称,或许今古一脉。物竞天择,姑娘儿的主产区缩减至东北,姑娘儿的称谓也随之方言化,因而引发坊间学界的疑议和猜详。
那么,姑娘儿怎么“咬”呢?
在结蒂处开个小圆孔,慢慢揉挤出果肉和果汁,保留完整的果皮。将果皮含在嘴里,唇齿舌喉腮齐“心”协力令其充满空气,再将开孔处抵住下唇黏膜,慢咬令其排气发声。如此循环往复,伴随姑娘们的青葱时光。
小链接吴歌,曾用名吴戈。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高级经济师。锦州市“最佳写书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锦州方言”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语言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摄影协会会员。金融专业论文和业余摄影作品,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奖。散文《丁香雨》入选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赛努呼和浩特系列文集·散文集》。出版专著《东北方言注疏》(白山出版社 2016年)。参加编著《人文锦州·民俗风情卷·锦州方言》(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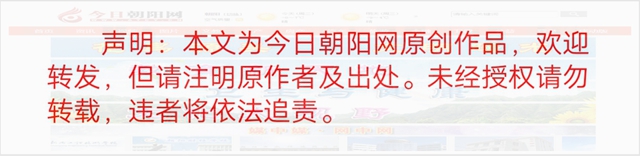
[编辑 冠群 编审 春语]








 春节不是年(吴歌)
春节不是年(吴歌) 【今日朝阳网】怠〔dāi〕之新证(吴歌)
【今日朝阳网】怠〔dāi〕之新证(吴歌) 爷娘与尊卑(吴歌)
爷娘与尊卑(吴歌) “憋亮子”异说(吴歌)
“憋亮子”异说(吴歌) “亮子”两说(吴歌)
“亮子”两说(吴歌) 傻姑爷子吃鸡(吴歌)
傻姑爷子吃鸡(吴歌) 【今日朝阳网】奇葩娱乐:咬姑娘儿(吴歌)
【今日朝阳网】奇葩娱乐:咬姑娘儿(吴歌) 儿化也有不归路(吴歌)
儿化也有不归路(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