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菜窖
文/管丽香(辽宁建平)
如果不是送菜的外甥女提起,对于菜窖的记忆或许永远不会再回到我的脑海中。
外甥女憨憨的,长着一张和她母亲一样的脸。几十年之后,我们竟然在一个住宅小区相遇。她声调低低地,试探着喊了一声老姨,我回过头瞬间,仿佛一下子见到了我从前的大姐,只不过她脸上的皱纹更密更深了些,这使我惊讶万分。眼前的这个外甥女也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没比我小上几岁,为了填补家用,她一直在帮别人带小孩。她是我一个叔伯大姐的孩子,可惜我那个大姐三十几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从血缘上讲,我们的关系不算远,她的热情纯朴和直率仍然保留着我们姐妹的某些基因。
我们相互惦记着。
偶尔,她会绕道刻意来到我的家门口,但说不上几句话就被淘气的小男孩拽走了。北方的冬天很冷,入冬以来接连下了几场雪,到了腊月更是滴水成冰。外甥女和孩子,浑身上下包裹得严实,一老一小圆滚滚的,直到他们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公园的树丛中。
一晃到了年根儿。冰天雪地的一大早,就见台阶下一个满头冰霜的人,正在吃力地从电瓶车上往下拿东西。我并没有太在意,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扭头往屋里走,听见有人喊我,跟着声音人已经蹬上了台阶。“老姨,是我!”外甥女一手抱着几棵大白菜,一手拎着一兜子绿萝卜,她回了趟农村老家。白菜萝卜都是自己家园子的,萝卜上挂的泥土是起早从菜窖扒出来带的,她嘱咐我放心吃,随即匆匆忙忙走了。我有一肚子感激话没来得及说。看着厨房堆起的绿色,我突然对农村菜窖燃起了一种崭新的热爱。
菜窖是北方农村用来存储冬菜的地方,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至少存在上千年的历史。三四十年前,我的农村老家几乎家家都有菜窖。在那片黄土地上,菜窖星罗棋布,可以说它曾经是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洞穴,同样上演过悲欢离合的故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菜窖尚处在兴盛时期。农村家庭过日子,没有一口像点样的菜窖心里终不能踏实,更别说在众人面前获得体面。某种程度上说,菜窖直接反映着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间接地印证着这个家庭在村子中的社会地位。人们在对待菜窖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还是颇费心思的。
我们那里的菜窖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寻一处向阳的沟坎子往里掏个窑洞,一人来高、两米多长,窖口放上一个简易的栅栏门。栅栏门就是个形式,挡君子不挡小人。夏天一到,窖门一敞可着劲地晒,窖堂里的土块晒成了古铜色,像极了父兄们厚实的胸膛。农闲时节,大人躺在门洞子里享受着清凉的过堂风,孩子们就藏到窑子里消耗精力。偷瓜摘枣的满足,都成了我们日后最美好的回忆。菜窖的另一种形式叫挖菜窖。挖菜窖比较复杂,动静大,有点像盖房子。尽管它费时费力有着诸多的难处,但大多数人家还是愿意在房前屋后找块合适的地方挖菜窖。秋末冬初,冻土立住层以后才能动手。标准点的,一间屋子大。菜窖上梁的圆木最好选用檩木,檩木上均匀密实地铺一层秫秸,再盖上厚厚的土层,结实又暖和。菜窖都要预留出一平米左右的窖口,竖下一根木制梯子,是上下的通道。挖到地里的菜窖要达到两米多深,浅了容易冻透,青储的菜再吃起来有一股味儿,这一冬的日子就全毁了。
当年,为了拥有这样一口菜窖,父亲忧心了好长时间。原来继母一个人的日子,院子还算宽敞。忽然来了一大家子人,鸡飞狗跳的立刻没有了下脚的地方。继母甚至提议把那棵占了大半个园子的梨树砍了,可以腾出一块很四至的地方。父亲认为损失太大。院子里除去搭建猪羊圈、鸡舍、狗窝外,仅剩下很小的一块地用来种菜。一大家子人没有菜吃,在农村就算不上过日子人家。
秋菜罢园后,霜气越来越重。早晨起来,流霜扑面,大地白茫茫的清冷。夜里的大风把垛在屋檐下的白菜萝卜刮落了一地。节气不等人,父亲在早就看好的地址上转来转去。外来户担不了沉重,他选中的地方虽说是村子的荒地,但实际上是掌握在梅姓家族的势力范围。本来他们就不同意我们的投奔,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父亲实在不愿再去揭那块伤疤。
我的大姐夫,就是送菜给我的外甥女的父亲,是梅姓的晚辈,他就住在继母家的前趟房。他年轻气盛,和父亲一起在村子里的学校教学。我家的难处他都看在了眼里。
大姐夫唤父亲三叔。他说,三叔你想在那挖就挖吧,就说是我家的菜窖,明天我帮你一起干。大姐家孩子多,日子过得很穷。大姐夫在他们的家族里人微言轻,他用他有限的力量为我们挺举着一片蓝天。
风声很快传到了梅奶奶的耳朵里。她是梅姓家族实际的掌门人。她七十多岁依然精神矍铄,她移动着三寸金莲一遍又一遍地掂量着,绕来绕去不肯走。以她的精明或许早已看出她这个教师侄子的“诡计”,但她又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侄子暗度陈仓。她的侄子确实没有菜窖可用。直到她的小儿子来喊她回家。她的小儿子十八九岁,皮肤黑幽幽的,一排齐齐的牙齿白得发亮,长得敦敦实实,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他来到后跑前跑后帮着忙活,嘴巴甜甜地跟着父亲叔叔地唤着。最近半年来,这个毛头小伙子有事没事的总爱往前凑,似乎在有意和父亲打着进步,但凭着两个家庭现在的紧张关系谁也不会多想。后来,在我家二姐去城里订婚那天,他也从家里跑了出去。家族遍找。第二天在山里一个废弃的石头窑子里发现了他,他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哭的抬不起头来。再后来听说,他早已喜欢上二姐并暗送秋波,而含苞待放的二姐却从未知晓。一段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的凄美爱情,就这样被各自放在了自己的心窝。
在霜冻来临之前,我家的白菜萝卜,土豆子都顺利地下窖了。菜窖堂口大,足够两家用。父亲吩咐我去大姐家,我嫌累,就站在院墙外扯着嗓子喊,催促他们尽快把青菜下窖。那一大家子人,七八个孩子挨肩儿的,一个比一个皮实。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才五六岁,全靠着大姐夫当民办教师那点收入养活。露着膀子、光脚丫的,炕上地上乌泱乌泱的。大姐苦笑着说,我们家从没窖过菜,日子过不了多久就吃光了。
后来,那个梅奶奶还是知道了菜窖的真相。她没再像以前一样在大姐家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他们。
转年夏天的一个晌午,大家都在大柳树下歇阴凉。大姐在树下捡到一个钱包,她认得那个钱包是梅奶奶的。大姐没念过多少书,心眼实在,她怕梅奶奶着急,就急忙打发孩子把钱包送归老太太。谁知祸起钱包,老太太一口咬定大姐偷了她的钱,并破口大骂,闹得全村沸沸扬扬。老实的大姐是百口莫辩,她知道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大姐做事向来黑白分明。一口气憋的她昏天黑地,她疯了。
大姐嘴角泛着白沫,不停地絮絮叨叨,说些什么她已经无所谓了。她领着她最小的孩子,就是送菜给我的外甥女,没黑带白挣扎着往外跑,似乎是想找到一块可以洗清她冤屈的地方。一人多高的苞米地、高粱地,齐腰深的谷子地,她不分时间地穿梭在青纱帐里,啃过青苞米,喝过沟渠的污水,我那个小外甥女跟在母亲的屁后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所幸的是,这些心酸都发生在她似懂非懂的年纪。
不久,我的大姐倒在了秋天的高粱地里,仰面朝天。此刻她应该完全放下了,卸下了压在心上的所有沉重。在她闭上眼的一瞬间,她一定看到了蔚蓝的天空中飘过的朵朵白云。彼岸花啊,快为这个苦难的女人绽放吧!
大姐走了以后,我们两家的联系就很少了,直到后来各奔前程失去了联系。
正月里,超市的菜价高的离谱。我几次走到菜架旁都没敢出手。蒜苔、韭菜、苦瓜等细菜我基本上都是绕着走。类似于白菜萝卜等大路菜,也是我五十多年第一次经历过的贵气。这个时候,外甥女雪中送炭,再次给我送来了新鲜蔬菜,而且是刚刚从自家的菜窖里扒出来的,泥土的芬芳尤其让我沉醉。四十多年了,现在的农村已很少有人家保留着窖菜的习惯了。
这一次,她有空坐了下来,扯起了遥远的往事。我说,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好多事你还记得吗?对于这个外甥女我始终怀有一种歉疚。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好多都记不得了。你还记得你母亲的样子吗?说到这里,她突然哭了,泪水汹涌而至。斜射的阳光洒在她的头发上,洒在她的身上把它镀成了金色的雕塑。
小链接管丽香,汉族,1966年出生,辽宁省建平县人。辽宁省作协会员、朝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建平县原文联主席。先后在《海燕》《辽河》《芒种》《中国绿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随笔80余篇,主持编辑出版了《清代喀喇沁右翼蒙古王陵石雕艺术》《建平民间艺术》《建平文艺群英谱》等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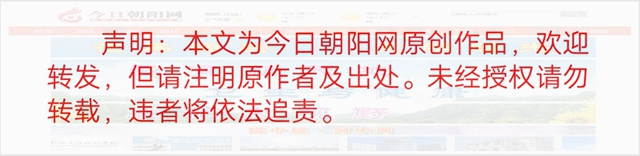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怀念凌源小吃(李文静)
怀念凌源小吃(李文静) 闲话饺子(李文静)
闲话饺子(李文静) 天地“粮辛”(孙玲玲)
天地“粮辛”(孙玲玲) 春饼(郭立萍)
春饼(郭立萍) 饺子里的花生米(董军)
饺子里的花生米(董军) 小米情思(李文静)
小米情思(李文静) 美食美客,咀嚼百味人生(晏春华)
美食美客,咀嚼百味人生(晏春华) 十一来啦!安平农场邀您采摘葡萄
十一来啦!安平农场邀您采摘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