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与磕头
文/文化信使 史庆友(辽宁阜新)
拜年是故乡人过年重要的一环,拜年是从年夜拉开序幕的。
拜年可有好多的说道:腊月三十晚上子时是真正的过年。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那时候拜年正当时。除夕夜晚十二点的时候“年三十晚上吃饭,没外人”,一家人都回家过年啦!十二点一过,“年”来了,一家人可以互道平安!给列祖列宗的牌位磕头,给长辈磕头,这时候家庭内部的拜年开始了。拜年之后才能吃饺子。
在我家,午夜的鞭炮燃过之后,父亲带头给爷爷磕头。身躯高大的父亲大嗓门儿,从外边放过鞭炮之后,进屋不论爷爷是坐是卧,大声地喊着:过年了,给大大(父亲的俗称)磕头了!随后父亲会双膝跪地,实实在在磕个响头。爷爷那边几乎是没什么反应。
爸爸磕完头,我和弟弟给爷爷拜年,也磕头。这时候的爷爷一脸的微笑,会打开他平日轻易不打开的小箱子,掏出几个早就用红纸包好的,里面有面额不大的钞票红包给我们。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压岁钱。压岁钱是那个年代小孩子一年中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一笔“大额”资金。
以前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多是一百文,寓为“长命百岁”;如今,许多长者喜欢选用连号的新钞赐予晚辈,有“连连好运、连连高升”之意,压岁的习俗源远流长,是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
现在想想儿时拜年磕头的场面真有趣:男孩子磕头实惠,也不管地干湿,着实一跪,脑袋磕到地上咣咣直响,有时脑袋都起包,女孩子不磕头。年轻媳妇特别是新结婚的,给老人磕头是必修课。
初一清早,全屯人相互拜年开始啦!
年轻人成群结队地走,几乎是一家挨一家地拜年。那个时候平日里人缘好的家庭去的人就多,平辈人见面作揖,嘴里说着“过年好”“新年好”!给谁拜年,就是给谁送去祝福。正月初一来拜年的如果是童男童女,将是大吉大利。家家都喜欢。
本屯子的孩子们给邻居们拜年不给压岁钱,只给糖块、瓜子、干果等小食品。乡亲们信奉送吉祥的来了,不能空着手走。给多给少是个意思。
记得那年后院王家的一帮孩子到我家拜年,有个小孩磕头后不走,母亲一想,原来是忘了给糖块了,忙抓了一把给装进兜里;还不走,他又瞅一眼桌上的瓜子,母亲又抓了一把瓜子给他。走了,却没走远,小孩走到了院里开始蹲下逗小狗;父亲一想,这孩子肯定还有心事:桌上还摆着一盘杏干呢!小孩褂子裤子上下四个兜都给他装得往外流淌,才紧紧捂着离开我家。
聪明的孩子不结帮拜年,而是单独去拜。孙家孩子也是一群,呼呼啦啦地到了我家拜年磕头,零食没来得及分发,大的领着小的就急匆匆离开;有个小家伙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进屋就磕头,说刚才慌忙没磕好,得重新磕。父母哈哈大笑,一把拉了起来,说别磕了,赶紧吃糖。
孩子们拜年为了贪吃,手段简单明了;而有些大人则是贪婪心理,虽然也是装模作样地来家里磕头拜年,但一眼就能看出其目的。
后院有位远房表弟,同我年龄相差不大,却十分喜欢到我家磕头拜年,常常三十晚上我家还没来得及揣元宝(吃年夜饼子)他就来了,进门后先是寒暄几句,一定得给我爷爷、他的大姥爷和我父亲、他大舅磕头。那时间正是我们揣元宝的时间,父亲说来了就别走了,坐下喝一杯。他会说我家刚揣过元宝,喝不少了,眼睛却盯着桌子上的酒瓶。当爷爷说喝点吧,大过年的,不能空嘴走。那好,那就喝一杯。没有废话,一仰脖子,一杯酒进肚了,一抹嘴,说好了,走!似乎很坚决。父亲说:怎么没唠嗑就干了?再喝一杯。那就再来一杯,这是最后一杯呵!他又很坚决。父亲说行,最后一杯。就这样一杯一杯地没有最后,最后常常是他老婆找上门:说是给大姥爷拜年了,年年来,年年喝多了,怎么见了酒比见了祖宗都亲!就这样,表弟在弟媳的叫骂声中,歪歪斜斜地出了我家,走时竟还能一次带走几支烟:两耳各夹一支,手里攥着,嘴里叼着。
又想起我更小的时候,爷爷领我去老家。我家在我们家族中是长支系人,辈小。那天是正月初三,刚好一位老人过七十三大寿,一屋子人,几乎都比我辈大。爷爷给我介绍一位,我给磕个头,后来我干脆跪着不起来了,介绍一位我点一下头,人们说我是磕连环头。那天我还真收到了压岁钱,那时候给的压岁钱有5分的,有1角的。放到现在是不多!但当时在生产队上一天班年底分红还有挣不到5分的,5分钱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少了。
关于拜年的年俗,还应该包涵姑爷到老丈人家拜年。在我们这儿,初二,姑爷要到岳父家去拜年,有已婚的,有未婚的。我想全国范围之内都应该有这样的习俗。
拜年,除了真诚问候以外,还有很多内容,比如拜年的姑爷要给岳父带礼物。在我小的时候,姑爷上门要带双“四盒礼”。不过是2斤糕点、2斤酒、2瓶罐头或2斤白糖或1斤茶叶就可以了,总计也不超过10元钱。别看钱不多,在那个年代买什么都要票,有的时候有票也没货,那可是纯粹的计划经济,商店营业员的一句“货没到”,会让人无言以对。
新姑爷来拜年,再忙也得住一宿,晚上老丈人要找多位小舅子陪着打扑克,那个年代没有麻将牌,打扑克也不来钱的,多是谁输了往谁的脸上贴纸条子或者是蹲着。常常是几个本地小青年联手欺骗一个外来人,脸上贴满纸条或长时间蹲着坐不下。那时候一家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老家拜年的习俗大抵如此,但现在的确比我小时候淡化了许多。小时候物资匮乏,生活贫困,非常期盼拜年。因为拜年时能得到不少零花钱或零食。
时光荏苒,这些陈年旧事早没了踪迹,虽然拜年磕头的习俗仍在延续着,但已经大打折扣了,年味似乎也淡了许多;时下多是给自家人磕头拜年,先拜自家长辈,再拜本族老人;即便在老家,邻居间那些成群结队的拜年队伍也不多见。
我喜欢那艰苦岁月中的磕头拜年。
(本文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经作者授权编发,编发时略有改动。)
小链接史庆友,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旧庙镇政府退休公务员,朝阳农学院毕业,省、市、县三级作家协会会员;市、县诗词学会会员,高级畜牧师。多年坚持写作,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文化内涵。有作品发表于《辽宁日报》等媒体。出版了散文集《心语》《心曲》,分别获蒙古贞文学奖、阜新文学奖。摄影作品《村头》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摄影展中荣获一等奖。在网络上发表作品200万字,多次参加网络征文并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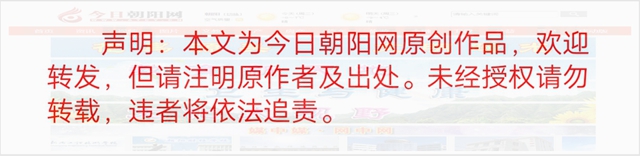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致童年时光里的那份快乐与天真(晏春华)
致童年时光里的那份快乐与天真(晏春华) 常驻校园的小鸟(谢晓丰)
常驻校园的小鸟(谢晓丰) 说说冯同事(杨秀兰)
说说冯同事(杨秀兰) 四月,抒一份美好(辛秀玲)
四月,抒一份美好(辛秀玲) 取一份人间烟火(辛秀玲)
取一份人间烟火(辛秀玲) 老了的时光(辛秀玲)
老了的时光(辛秀玲) 忆烟花(张美玉)
忆烟花(张美玉) 我家的“人世间”(杨秀兰)
我家的“人世间”(杨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