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爱
文/于春林(辽宁葫芦岛)
家乡是一个古朴的小村庄。以前,土地贫瘠,民风淳朴,全村有二百多户人家,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生活还能自给自足。
那时,大多数家庭的男孩子初中毕业就要回乡务农了。可我的父母只要我能念下去,就坚持供我上学。
那一年,我们村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很羡慕的事。可是父母却因为我的学费而犯了愁。但无论怎么为难,他们在我面前绝对不表现出来。
学校住宿需要自己带行李箱,我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哪有多余的钱买行李箱啊。
那天晚上,父母以为我睡着了,就压低声音说着话。
“把家里那口老柜子拆了吧,不然孩子的衣服往哪儿放啊!”母亲说。
“那口柜是咱们结婚时家里分的,板材很厚,我准备留着咱们百年后用呢,打一个箱子浪费材料了。”父亲语气中有些惋惜。
母亲略带责备地说:“你想得倒是很远,但眼下孩子的学费还得东挪西借呢,哪有钱再买行李箱啊。”
我听着父母说话,心里有些愧意。为了供我读书,父母吃尽了苦头,想尽了办法,两个姐姐都辍学上班了……想到这些,我眼角发涩,眼泪淌了下来,我把头悄悄地缩进被子里。那一夜我才懂得他们的良苦用心。
第二天,父亲招呼和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大伯父帮忙,把那口柜子抬到院子里。大伯父得知父亲是要把柜子拆了给我上学打行李箱时,生气地说:“你们两口子也忒顾孩子了,家里连学费都没有,读什么高中,趁早下地干活算了,还把家里的柜子拆了,心气太高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时我也帮助父亲抬柜子,大伯父的话仿佛锥子一般刺痛我的心,说得我脸直发烧,真想哭出来,告诉父亲母亲,我不想去上学了,这样也不必把祖辈留给他们的柜子拆了。但看着父亲被大伯父说得先红后白的脸,我没敢说出口。
那口柜子是朱红色的,确实很厚重。在那时,柜子是每个家庭的门面,大多数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每个家庭最普通的家具,特别实用:家里的衣服、有用的物品都可以放进去。记得母亲每天都会把这口柜子抹得一尘不染,逢年过节时,还要用上一点缝纫机油来擦,铮亮发光,很喜庆。
父亲抚摸着这口陪伴他们几十年的柜子,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深情。但为了他唯一的儿子上学用,他还是狠狠心把柜子的木板一块块拆了下来。我和母亲给父亲打下手,把拆下来厚厚的板子小心翼翼地放到一边。那一天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为了节省不必要的花销,父亲没有找村里的木匠,而是借来锯子、刨子、锤子等用具亲自给我打箱子。母亲还去供销社买来了钉子、砂纸、刷子和油漆。
父亲虽然不是木匠,但农家院里的活一般都能干得来。他干活时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许别人插嘴;院子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把邻居们都吸引过来围着看。母亲热情地招待他们,人们满脸羡慕的表情,嘁嘁喳喳地说着话,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好有出息,那热闹的场面是我们家很少有过的。
父亲用他粗糙的手做起了木匠的细活,显得很笨拙。但他努力地做好每一道工序,一点都不马虎,即使是一个榫卯都契合匀称。我发现父亲布满老茧的手磨得更加光亮了,虎口处还渗出了血。我了解父亲的脾气,没敢说什么,但心里热乎乎的。
整整用了半天时间才把箱子打完,而且打了两个一模一样、方方正正的行李箱,规规矩矩摆放在院子里。我很纳闷,就不解地问父亲怎么打两个行李箱。母亲告诉我,另一个是送给和我很要好的石磊同学的,他们的家境也不好。我听了母亲的话,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和感动。
父亲累得满头大汗,坐下来抽袋烟,休息一下。母亲就开始用砂纸打磨箱子,我帮助她用抹布擦净上面的木屑。然后母亲开始刷油漆,她特别卖力气,一遍一遍地刷,总共刷了三遍。油漆是天蓝色的,刷完油漆的木箱子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特别美观。
我上学用的行李箱,连同我同学的那只,就这样备齐了。我感觉,这个行李箱比世上任何一只箱子都昂贵,因为它里面不仅仅装着我求学时的衣服和书籍,还装满了父母沉甸甸的爱。
(本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作家报》,经作者授权编发,编发时略有改动。)
小链接于春林,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作品散见于《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劳动保障报》《长春日报》20多家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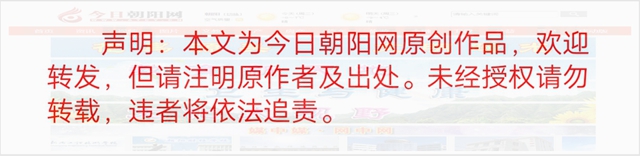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致童年时光里的那份快乐与天真(晏春华)
致童年时光里的那份快乐与天真(晏春华) 常驻校园的小鸟(谢晓丰)
常驻校园的小鸟(谢晓丰) 说说冯同事(杨秀兰)
说说冯同事(杨秀兰) 四月,抒一份美好(辛秀玲)
四月,抒一份美好(辛秀玲) 取一份人间烟火(辛秀玲)
取一份人间烟火(辛秀玲) 老了的时光(辛秀玲)
老了的时光(辛秀玲) 忆烟花(张美玉)
忆烟花(张美玉) 我家的“人世间”(杨秀兰)
我家的“人世间”(杨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