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夏日杏飘香
文/文化信使 沈兰香(辽宁凌源)
今夜,小城的雨从时光深处打马而来,带着清馨的熟杏气息。那些故园独有的天籁之音在这盛夏的梦里按下了重播键。
一阵风从南山的玉米地漫过来。隆隆的雷声滚过树梢,紧接着密集的雨脚奏响了蓬勃的旋律。有雨滴擦过黄麦草的房檐打湿了窗户纸。门框上艾蒿拧成的火绳明明灭灭闪动着点点火光,淡淡的烟气满屋弥散。母亲翻个身自言自语,“下雨了,玉米抱娃子了,秋天贴饼子了。”一会儿,风轻了。后院响起了“吧嗒、吧嗒”的坠落声,中间夹杂着骨碌碌滚动的声音,给原有的旋律配上了完美的和声。孩子们挤在火炕上迷迷糊糊地听着,睡着,嘴角漾起笑意。母亲对父亲说,“他爸,你听杏熟了,明早准是一地的水灵呢!”那声音里透着丝丝甜意。
辽西多山,稀稀落落的农家小院镶嵌在山的褶皱里。各家房前屋后都栽着好多果树。我最喜欢杏树。杏花一开,小村暗淡的底色里就幻化出光彩来。杏花刚落,那酸溜溜的小青杏就俘获了孩子们的味蕾。
我家后院的杏放暑假的时候就熟了,肥硕的杏子挂满枝头,煌煌地炫耀着夏日的富有。土坎边这棵树结的杏,果肉细腻绵软,一嘬一包甜水。靠墙的那棵是甜核杏。母亲把苦杏核攒起来,砸杏仁卖给供销社,买些粗盐、灯油之类的生活用品。用杏仁做粥或炖豆角也是难得的美味。我和二哥把晾好的甜杏核装在布袋里,闲来无事砸上一把,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地嚼着,唇齿之间涌动着满满的幸福感。母亲打发姐姐摘了杏给邻居送去。父亲上生产队干活挎上一筐杏,歇息的时候乡亲们围坐在地头吃。谁家的杏先熟,谁家的杏啥味人们心里都清楚。长在路边的杏树,不管是谁家的,路过的人摘了就吃是没有人介意的。
老爷爷家门前有一片杏树林。杏熟的时候,小老叔向左邻右舍传达大人的“指示”,“大嫂子,我妈说要晃荡杏了,让你们都去吃杏呢!”话音刚落,孩子们就跟在他身后一溜烟地跑到树下。三叔站在粗壮的树杈上轻轻一晃,那熟透的杏就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孩子们猫着腰捡地上的杏。又一晃,那杏就不管不顾地砸在后脑勺上,光着的后背上,孩子们一声高过一声地“哎呦”着,嬉笑着,边捡边往嘴里塞。捡满一小瓢儿倒进老奶的大筐里。三叔晃完了这棵树又爬上了那棵树。大人们捡了杏用衣襟兜着,或者放在草帽里,坐在碾盘上边吃边咂摸滋味。这个是“酸梨果”,那个是“小蜜罐”,每棵杏树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外号张扬着个性。一个蹒跚学步的娃娃,抓起杏就往红肚兜里塞,刚从上面塞下去,就从下面掉了出来,如胶皮球般在地上蹦跳着跑出老远,惹得人们弯腰捧腹地一顿好笑。老奶拿来小板凳、蒲团,婶子大娘们吃完杏就坐在树下呲呲啦啦地纳鞋底,唠家常。叼着旱烟袋的大伯挽起裤管,斜靠在杏树上悠然自得地吐着烟圈。一阵风送来清凉,也吹远了流年。
窗外的雨还在下着,那些在杏树下长大的孩子早已走出小村的庇护,奔波在不同的城市。唯有儿时记忆中的乡村物事,不时涌动着至真至纯的人间情味熨贴身心。
(此文发表于山西《枣花报》,经作者授权编发,编发时略有改动。)
小链接沈兰香,笔名杏花雨,辽宁省凌源市人,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有诗歌和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化报》《今日朝阳网》《辽西文学》等网络平台和纸刊发表,曾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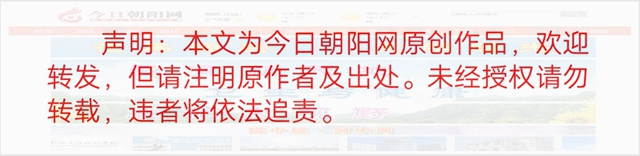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怀念凌源小吃(李文静)
怀念凌源小吃(李文静) 闲话饺子(李文静)
闲话饺子(李文静) 天地“粮辛”(孙玲玲)
天地“粮辛”(孙玲玲) 春饼(郭立萍)
春饼(郭立萍) 饺子里的花生米(董军)
饺子里的花生米(董军) 小米情思(李文静)
小米情思(李文静) 美食美客,咀嚼百味人生(晏春华)
美食美客,咀嚼百味人生(晏春华) 十一来啦!安平农场邀您采摘葡萄
十一来啦!安平农场邀您采摘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