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脚步
文图/文化信使 沈兰香(辽宁朝阳)
“妈!妈!” 我用力抱紧双臂,两腿不住地颤抖,拼命地喊。嘴里叼着的玉米面饼子跌落在地,扑向我的野狗一口吞下饼子,扬长而去。我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个梦。一阵凉风从窗外袭来,两声闷雷响过之后,雨又下了起来。我重新记起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暗夜无眠,听声声滴落的回响,是雨,是泪,是血……
1936年出生的母亲三岁就没了娘。大舅比母亲大三岁,大姨比母亲大六岁。姥爷是石匠、瓦匠兼粉匠,常年奔波在外,只好把年幼的母亲寄养在三姥爷家里。母亲九岁时,姥爷给这三个苦瓜秧上的苦孩子找了个后娘。母亲又回到了家。后姥姥又领着三个苦瓜蛋子进了门。三个姨都比母亲大,后来又有了老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一大家子人能吃上饭已是奢侈。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她常骑在学校的土墙豁子上听着草房子里的朗朗书声。她和我们说,她没喝过“蜜水”,一个大字不识。听得出,她那话语饱含着渴望。大姨出嫁之后,她常偷着跑二十多里山路去找大姨,回来之后就要领受一顿树条子、圪针伺候。
野生野长的母亲十九岁骑着毛驴嫁给了素未谋面的父亲。从西山坡移栽到了东山岗。父亲和母亲同岁,是读过书的文化人,但少言寡语,一脸严肃。爷爷倒还慈祥,可奶奶却是个讲究规矩的婆婆。大姑已经出嫁,二姑、老姑、二叔还在念书。父亲是家中长子。母亲像裹着小脚似的颤颤巍巍地迈进家门,不敢少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没日没夜地放下田里活,拿起屋里活,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还常常受到奶奶的责难。
大姐、大哥之后,二姐出生了。从没蹲过灶坑的父亲亲手炖了一碗粉头咸菜,煮了两个鸡蛋端上炕。母亲当时受宠若惊,满眼闪动着对父亲的感激,心里暖暖的。她想,总算可以好好地坐回月子了。正在此时,二姑婆家派来给娘家报喜的人到了,说二姑生了个大胖小子。老姑听了,把炕上的炖咸菜和鸡蛋装进筐里,拔腿就跑,给二姑送去了。日后才知道二姑的孩子是抱来的。母亲说,自己从小没娘就是没有口福的命,要不咋就赶得那么巧。
后来又有了二哥。我最小,是父母的“老娇子”。我是“坐生”。母亲在生产队种了一天的地,晚上父亲去队部开会,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的土炕上摸着阎王爷的鼻子生下了我。
大姨婆家那个山沟沟叫荒地,山地薄打粮少,吃水还得用驴到好几里地远的山外驮。家里有四个儿子,生活艰难,决定举家去黑龙江投奔小叔子。母亲是背着我走了二十里山路去送大姨的。大姨喜欢姑娘又可怜母亲身体孱弱,要带我去黑龙江。母亲先是答应了,等大姨抱着我走远了又发疯似的追上去,把我要了回来。大姨刚到黑龙江常有书信往来,读信写信都是父亲的事。信里说,大姨夫到那不久就因水土不服去世了,大姨的四个儿子也没了一个。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寄出的信都被退了回来。母亲惦念大姨,一颗心像吊在辘轳上的水桶悬着放不下来。
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每年都养两头猪。一出正月,父亲就去集市抓来两头小猪崽。一家人从嘴里省出些稀粥、菜汤喂养它们。杏花开过,小叶椴就长出嫩叶。母亲和梁后二婶,张家大娘,刘家二娘早早约好。生产队去沟里薅苗的时候,母亲和她们结伴趁中午歇晌,去“跳石坎”的“烂石窖”边上捋小叶椴叶子。捋满一口袋扛下山就躺在地头,从衣兜里摸出早上从家带来的玉米面饼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眼前的一坡青苗晃动着云影般的盼头。哨子一响接着薅苗。晚上散工,母亲把口袋扛回家,先给猪撒两把小叶椴叶子,然后再洗几捧,撒上盐,拌上玉米面上锅蒸小叶椴布拉。馇一盆高粱𥻗子粥。一家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围着桌子吃得热汗涔涔。刷锅刷碗的水趁热舀给猪喝。等榛柴长出嫩叶,大姐、二姐放学就去山上捋回来喂猪。我和二哥常挖些苦麻子、刺菜给猪吃。 八月节过后挑一头大的猪卖给国家,送猪的时候,母亲端着泔水瓢跟在后面“嘞嘞嘞”地叫着,一直送到西梁头,回来把泔水倒进猪槽子,期待明年还能养出这样不挑食的好猪来。剩下一头小的再喂上一冬上上膘,过年杀猪吃肉,这就是全家人一年的油水了。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父亲放弃了民办教师工作,踌躇满志地和母亲一起种地、养羊供我们几个孩子读书。大哥到了成家的年龄,父亲张罗着拆了草房,为大哥和二哥分别盖起了三间瓦房。
日子如山泉水般汩汩地向前流着。大哥、大姐、二姐相继成了家,直到最小的我领着孩子住姥家的时候,二哥还没有结婚。我们住的小村隐在辽西群山的褶皱里。我们这群孩子是哼着“一进东干沟步步踩石头,一进干沟门稀粥两大盆……”这个顺口溜走出童年的。现在虽然山还在,石头还在,童年的余音还在,而我们这个山旮旯已然盛不下这一代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
二哥的对象看了一个又一个,姑娘们都望山兴叹,选择放弃。媒人说要是房子盖在山下的道边或许能成。父亲恨不得把这房子安上轱辘推到山下去。后来,二哥去长春批发本地苹果和一个姑娘两情相悦。姑娘父母只有三个女儿,结婚就得去长春生活。姑娘家里催着要订亲,二哥硬着头皮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家里大小事情一向是父亲说了算。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小心翼翼地看父亲的眼色行事。母亲心里犯了难,揣摩再三把这事和父亲说了。父亲听后大发雷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去做别人家的上门女婿。父亲没收了二哥所有的钱,不准他再去长春。母亲眉头拧成了疙瘩,在日暮时分,眼泪汪汪地站在门前的高坡上默默地凝望遥远的天际,努力想象着山外面的世界。夕阳余晖拉长了一个日渐佝偻的侧影。二道洼刮来的风蹚过玉米地重复着一声声叹息。在一个秋天的黎明,鸡叫两遍之后,母亲趁父亲还在睡觉,把自己刨药材、捡蘑菇卖了攒下的零钱塞给了二哥,偷偷放走了他。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母亲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她也会走出这个山沟沟。
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更多农村人不失时机地涌向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大哥和我们三姐妹也举家奔赴不同的城市。二哥和二嫂在长春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上辛勤耕耘,种菜、卖菜,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年逾古稀的父亲和母亲笨手笨脚地侍弄着几亩山地。母亲一有空就站在家门前翘首远望,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树,一棵被岁月和离愁压弯的树。
2009年5月,我们怀着深深的愧疚和悲痛送走了父亲。二哥把母亲接到长春安度晚年。二姐也把家搬到了长春。大姐、大哥和我每年都接母亲到自己家住上几个月,后来母亲年龄大了不堪长途劳顿,我们便不敢再接。几年之后,长春市扩建新城区,二哥原来的菜地如雨后春笋般长出一幢幢高楼。母亲也住进了楼房。我们常在视频里聊天,听母亲念叨老家的柴火大灶,小豆腐,黏豆包。此时,母亲眼神里流露出对旧日时光和农家生活的眷念。
一个夏天的午后,二哥拨过视频,画面里一个大院子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玉米和各种蔬菜。院里支起一个大锅,锅里的水沸腾着,鲜嫩的玉米宛若一群游鱼咕嘟咕嘟地吐着泡泡。隐约有一股熟稔的香气隔着手机屏幕袅袅地飘过来。“难以抗拒的诱惑啊!”我不禁感叹。灶间锅台上放着满满一盆红烧肉。另一个盆里一双手和着炸丸子的豆腐。一缕白发拂过屏幕。我诧异地问,“这是哪?”二哥说:“我在郊区买了个大院子,今儿我们喊着楼上楼下的邻居一起来尝新鲜。老妈特别高兴亲自动手给我们炸丸子呢!”母亲眉欢眼笑,对着视频翘起了三个裹着面糊的手指头,得意地说:“我老儿子有仨家!”旁边的二嫂搭了腔,“仨家咋地,也是一个老婆一个娃!”逗得身边的人都笑了。母亲的脸笑成了一朵带露的菊花。
那些年和大姨失去联系之后,大舅亲自跑一趟黑龙江才找到大姨。时隔半个世纪,黑龙江呼兰家家户户都养牛,大姨家的表哥已是一位资深的兽医了。二哥开车带母亲去和大姨团聚。两个银发老人偎依着,在东北的热炕上同宿同餐,老姐妹俩相伴了两个多月,了却一桩心事。
母亲八十大寿我们兄弟姐妹聚集到二哥家。我们众星捧月般围着母亲叙说童年。当点燃生日蜡烛,唱起生日歌那一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涨满心海。尽管我们鬓发苍苍儿孙满堂,有母亲在,我们依然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母亲的目光拂过在场的每一位亲人,舒心地笑了。这是母亲一生中最盛大、最隆重的生日。
2021年5月,母亲走完了她八十五岁的人生之路。母亲从旧社会走到了新中国,从辽西丘陵沟壑走进东北黑土地的辽阔,亲历了那一代人波澜起伏的人生际遇。母亲说过,她知足了,赶上了好社会,过上了好日子。
期待已久的高铁开通了,老家的路也修到了家门口。而母亲却离开了我们,写到此处禁不住泪雨潸然……
小链接沈兰香,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辽宁省凌源市人。有诗歌和散文在《辽西文学》《朝阳日报》《燕都晨报》《德州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纸刊发表,曾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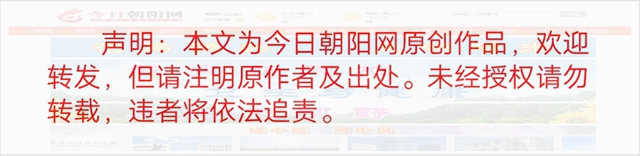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母亲的脚步(沈兰香)
母亲的脚步(沈兰香) 品茶,品出人生真谛(王铁兰)
品茶,品出人生真谛(王铁兰) 十赞祖国的航天(华玉玺)
十赞祖国的航天(华玉玺) 我家的小菜园(王文月)
我家的小菜园(王文月) 而今迈步从头越(华玉玺)
而今迈步从头越(华玉玺)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晏春华)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晏春华) 妈妈的兜(杨秀兰)
妈妈的兜(杨秀兰) 又是杨花飘起时(李文静)
又是杨花飘起时(李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