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二章 生命的本色——写给父亲
父亲那一代人用全部生命演绎了一个群体的品格:一种在极致状态下诞生的极致品格,类似石墨在高温高压之中变成金刚石一般,令后人难以企及,无法复制。

真正的认识,从父亲逝去开始
1973年,我还是一个新兵。
一次部队集训,师宣传科科长讲课。科长戴眼镜,四川口音,嗓门很大,讲话极富鼓动性。听得津津有味之余,他突然提到父亲的名字,令我颇为吃惊。他说解放初期参军进学校,父亲给他们讲了第一课——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社会,劳动创造了世界……他印象极为深刻,这是他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启蒙。
宣传科科长在台上讲得绘声绘色,我在台下听得呆若木鸡。
当时,父亲尚未恢复名誉,宣传科科长也想不到会场里竟坐着他的儿子。我作为新兵,敛声屏气坐在那里,内心激动万分:这是在讲父亲?父亲真的这么厉害?我怎么就不知道?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呢?他讲的事情怎么能让这位科长多年念念不忘?
很长一段时间,我脑海里都在反复回味宣传科科长讲的每一句话。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其实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父亲。
1983年,父亲病重住院,在病房里,我生平第一次给他洗脚。脚上一块块老皮,洗起来硌手,这又一次让我惊异。印象中父亲他们这样的干部,进出办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红旗车,脚上怎么会这么粗糙?
父亲当时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
他告诉我,红军长征时期,有一段连草鞋都没得穿,脚板上磨出了厚厚一层老茧。行军下来,抬脚一看,厚茧中又嵌进许多小石、尖刺。开始还往外抠一抠,时间一长也顾不上了,就这样赤脚行军,赤脚冲锋。最困难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机枪连,不但要光脚行军,还要扛沉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走小路或爬无路的山。一直到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二军团的同志才给了草鞋穿,才能够不再光脚走路。
我一边给他洗脚,一边抬起头来惊讶地望着他。该怎样把当年那个赤脚行军、赤脚冲锋、赤脚扛马克沁重机枪的他,与眼前这个被各种现代化医疗设备包围的他相联系?该怎么将现在扶着拐杖才能走路的父亲,与当年那个闯过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的父亲相对照?
我曾经看过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描绘孩子对父亲的认识:
10岁时说:“爸爸真伟大。”
18岁时说:“父亲也还行。”
25岁时说:“老爸不过如此。”
30岁时说:“老爸真是糊涂透顶、愚昧透顶!”
38岁时说:“父亲的话也不是一无道理。”
45 岁时说:“怎么老爸当年就把这点事儿看透了?”
55岁时说:“哎呀,我的父亲真是了不起!”
这段话幽默地描述了一个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对父亲的认识的改变。我们对父亲的认识没有经历这样的马鞍形,走的是一条类似蓄电池充电一样的上升路径。
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回老家。
虽然在相册中看过老家的照片,但身临其境,感觉还是十分新鲜。家乡贫困,但乡亲真挚热情,走到哪里都是醪糟鸡蛋招待。
到了父亲出生的金家村,虽然早有思想准备,绵绵阴雨中我还是惊呆在几间潮湿破旧、屋里黑到几乎难有一丝光线的土坯房前。这就是父亲当年生活的地方。与我们在昆明的住房、在北京的住房有着天壤之别。
姑姑站在屋外等我,拉着我的手不放,从来到走,始终泪眼婆娑,不停地用大襟上系的手帕揩泪水。
我记不得当时乡亲们都问了我什么,姑姑又跟我说了什么,四周乱哄哄的喧闹之中,头脑里盘旋着一堆问题:当年父亲以什么心境从这里出走的? 1959 年回故乡又是怎样的感觉?他的表面风光与荣耀人们都看得到,他的内心纠结与苦痛谁又了解?他穿了一辈子军装,什么是他生命的本来颜色?
对父亲的真正认识,就是当他逝去后,从这些众多的疑问开始的。
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8年了,我也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描述中国革命艰难岁月的书籍《苦难辉煌》,获得不小的社会反响。
母亲曾经感慨地说:“你父亲要是在,看到这本书就好了。”母亲的意思是,书中写了父亲他们这代人想弄清楚而一直没有条件弄清楚的许多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通过完成这本书,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父亲那一代人,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
我常想,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果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五次反“围剿”,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他们这些人的命运又会怎样?
如果没有这一切,父亲生命的轨迹肯定会向其他方向延伸。他可能终生务农,也可能靠着上过几年私塾,有幸当个小学教员,做个孝子,在家乡给奶奶养老送终,安安稳稳、平平淡淡直到生命的终结。
但是有了这一切。
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1930年6月,红军攻克永丰,父亲得讯立即奔向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之前,奶奶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
“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来养老的。”
但他还是毅然出发了,走上一条终生不悔的道路。
在民族命运空前危机的时刻,父亲他们这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空前奋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国救民的行列之中,从而也就失去了安逸务农、持教、经商、从政的条件,最终成为一批震惊中外的革命者。
军旅作家朱苏进说得好:“那个时代的将军,都是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他们是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求生,而不是出于对军人职业的嗜爱、不是为了出仕为将才慨然从戎的。这就使他们的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彻底性。”
的确如此。他们对事业具有一种极其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忠诚。
红军时期,父亲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团政委一下子撤到文书,连降7级,一度还被怀疑是“AB团”,差点儿丢掉性命。就是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这条道路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到那么大的磨难,被无端扣上“三反分子”“贺龙分子”等一大堆帽子,但他也不允许别人置疑这个党、这个军队,不允许别人置疑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领袖。
不管一生如何风云变幻,他对这个原则的坚守却一直稳如泰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的队伍里”!
1979年,我在南京学习,父亲去福建途中正好路过这里,就把我也捎上。这是我第一次随他外出考察。一路上他反复念叨“漳州、漳州”。随行的人都奇怪,好像有什么重要事情在那里等他。
漳州到了,他不顾长途颠簸疲劳,下车就去找一个广场。大家跟着他转了半天,才在一处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停了下来。他眼里晶莹闪亮,说:“就是这个地方,变样了,都变样了。”接着他向大家讲述: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讲话。47年过去了,他百感交集。
父亲平时不喜欢照相,这回却没有反对给他拍照。走到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他破天荒地提出:“在这个地方留个影。”并且叮嘱:“一定要照好。”
他自己整军容。摸摸领章,正正军帽,然后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了胸。身后纪念馆那堵墙壁上,依稀可见当年红三军留下的大标语:“扩大红军”。
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压在家中大桌子的玻璃板下。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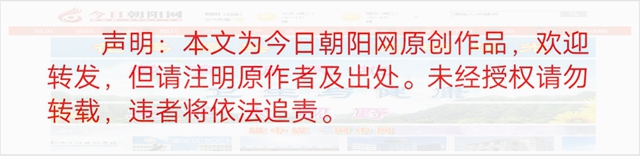
[实习编辑 关茗月 编辑 瑞雪 审核 雅贤 编审 春语]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