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三章 阶级叛逆者——写给母亲
人生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向往是什么?得到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完全弄清楚。

我心目中的母亲是个恋家之人。
每到周三周四,她就开始操心周末的饭菜,然后耐心等待子女一个一个回来。有事回不去,打电话“请假”时,我们都会忐忑不安,似乎看得到电话那一端母亲失望的表情。周末全家团聚,是她最重要的心愿。
然而,她对子女的关切,与别人的母亲又不尽相同。记得当年参军入伍时,母亲送我到新兵集结地点,与接兵的王连长简单讲了几句话,便很快离去,不像现场的其他母亲那样,与即将远行的孩子难分难舍,叮嘱个没完没了。我至今仍记得,在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中,母亲裹了一下围巾、头也不回快步消失在寒冬中的背影。
操持有6个子女的大家庭,她不知付出多少心血,也练就了那种说一不二、不容争辩的干练。她并不喜欢子女们整天绕在身边,希望孩子们能够各自独立飞翔。
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印象中当年那个忙碌、严厉、说话干脆、做事果断、个性极强的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依旧严厉果断、依旧个性很强,但日益增加了对子女的温情和眷恋。她希望子女们再忙,也不要忘记这个家。只要回家,不管讲什么她都爱听。如果不回家,怎样给她解释她都不高兴。社会风气不好,她不满意,但满意子女在单位个个争气,在家个个尽孝,有个好的家风。
父亲也是个恋家的人。多年工作繁忙,他很少有时间顾家,也少有时间享受家庭亲情。经历无数波折之后,父亲晚年对自己的家庭表现出一种难于言表的眷恋。
1972年底,他被关押5年之后终得释放。几个孩子即将参军出发,唯有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想留下来继续在工厂干。当了一辈子兵的父亲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听着母亲和大姐对我苦苦相劝。从眼神中能够觉察他不反对我的决定,不希望孩子们个个离他而去。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来。
后来听母亲说,我们都走了以后,父亲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坐在桌前,戴上老花镜,认真阅读我们从各地寄回家的信件。哥哥和我在部队立三等功的喜报,他放在中间抽屉里,有空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父亲革命一生,从来以工作为重,却也特别珍视自己这个家庭。1982年初,他大病一场,与死神擦肩而过。刚刚缝合被切开的气管,可以下床行走了,就不听别人劝阻,急着要回来看看离开了半年多的家。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父亲穿了件米黄色绸衬衫,戴着草编的遮阳帽迈进院落。在大家的前后奔忙之中,他拄着手杖,穿过光影婆娑的葡萄架,敞开衣扣,缓步向我们走来。子女们个个热泪盈眶,他脸上却绽放出那种从内心充溢出来的春天一样舒心、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心灵的驿站。家庭是身体的歇息地,是精神的放松地。不管外面如何狂风暴雨,这里都有你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小屋。不管外面多么惊涛骇浪,这里都有你一处安全靠泊的港湾。对子女来说,不管你在外面遭遇多大的挫折和委屈,这里都会倾听你的诉说,并给你加油充电。不管你在外面多么说一不二,回到这里你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受教诲。不管你长到多少岁,回到这里你都必须重新回归兄弟姊妹的长幼序列。
上学时,有一句老师用来批评学生的话:“家庭观念太重。”也许就因为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来一直上寄宿制学校,每周有6天都吃住在学校里,从小我就没有很重的家庭观念。
“文革”开始,我们几个初一的同学外出串联,到了上海,发烧40度,说是急性肺炎。一个人昏昏沉沉躺在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宿舍的上铺,也没有想家,只是懊恼不能和其他同学一起去转南京路和外滩。
参军入伍后,部队规定服役满三年就可以探亲,我整整四年才第一次提出探亲申请,主要原因还是毛泽东主席去世,想回北京了解情况。那是1976年冬天。到家后,母亲问我:“四年没回来,想不想家?”在部队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干得热火朝天,我真的很少有时间想家。但又怕说出来伤母亲的心,就回答说“想”。
又过去了三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像我这样家庭观念淡薄的人,也越来越感受到家庭在心中的分量了。我们全家人曾经天各一方——大姐在黑龙江尚志县,后来转到北京房山;二姐在安徽合肥,后又调到芜湖;三姐在内蒙古五原,后来去了云南;大哥在陕北宜川,后来去了贵州;我在湖北光化;弟弟在山西大同。母亲作为全家的轴心,用一封又一封家书,把天南地北的一家人紧紧地联在一起。
母亲的信很少儿女情长。她把“四人帮”在北京的倒行逆施告诉我们;把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的诗词抄给我们;把她对党和国家的深深忧虑传递给我们。后来回想,自己在偏远的鄂西北山区基层连队当机械员时,还能够比较敏感、比较清醒,按照今天的话说,还算“比较具有信息量”,母亲的一封封来信起了重要作用。
我开始悄悄在连队几个战友中间,传递母亲信中所说的事情。听后,大家个个情绪激动、义愤填膺。绰号“大胡子”的陈景乐按捺不住,竟然半夜一个人偷偷爬起来,去撕连队墙报上“批邓”的大标语。这件事他没跟我们说,却被起来上厕所的人看见。幸亏也是自己人,只悄悄告诉我们就了事。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帮他保密。但消息最终还是漏了出去。后来机关政治部的人跟我们说:“幸亏很快粉碎了‘四人帮’,否则你们连队已经被列为调查对象了,你们几个人都是调查重点。”
几十年过去,原部队早已撤销,“大胡子”陈景乐也转业回了山西。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我都能想起湖北老河口那个冰冷的冬天,他裹件棉大衣溜达到墙报底下,环顾左右没人,一把扯下墙上标语的情景。那已是我心中一幅恒定的图画了。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它依然在描述三十多年前,多少个像陈景乐这样赤诚的中国人,强烈要求国家变革的图景。
当时在他的央求下,我曾经给他看过母亲写来的信。母亲的字迹不像一般女性那么文静秀气。她的字写得大,写得快,写得扎实,既清晰又有力,字里行间透露着她那黑白分明的性格。“大胡子”陈景乐看完信后对我说:“你母亲真有水平。”
有水平,却不一定有机会、有时运。我总觉得母亲一生有些耽误。她始终没有处于一个能够发挥她全部能量的位置。也许除了机会和时运,还与她的脾气和性格有关系。
母亲的脾气很急,性格很硬。急,就容易伤人。硬,就容易折断。伤了且断了,一个家也就随着完了。父亲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临终前父亲曾经嘱托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母亲,担心她一个人能不能维持好这个家庭。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表述父亲、母亲对他们亲手组织的这个家庭的那种永远怀抱的希望和永远不断的眷恋。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告慰他:母亲做到了。子女们也都尽心尽力帮着母亲做到了。
在维持和维护这个家庭方面,十分惭愧地说:我做事不多,出力最小。非但如此,头脑中还时不时闪过某些叛逆的意向。自我解释可能是血脉相承。
当父亲母亲像所有的父亲母亲那样,要求我们听父母的话、遵守好家规、不要个人主意太大的时候,我总会蓦然想到当年父亲母亲是怎样离开他们各自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果他们都听父母的话而不离家出走,一个江西永丰的农家子弟,一个河南开封的初中女生,怎么可能前者经过万里长征,后者也是千里迢迢在延安会聚,在黄土高原完成他们的结合?
父亲在自传中这样叙述他离别家庭的情况:
“1929年我就下定了决心丢家革命,当红军去。”
“1930年春节前夕,红四军一个纵队打下了城。旧历正月初一,我瞒着家人,回避村人,从小路进城去找红军。”
父亲是家中的独子,明明知道“我走后家一定会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踏上了万水千山的里程。那一年他21岁。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奇特。不同选择造成的不同结果差异竟如此巨大。九死一生长征到延安的父亲,怎么能够想到千里之外的开封女中有一个学生,也即将离家出发奔赴延安,后来与他结为夫妻?
母亲回忆说: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开封沦陷,那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学校停办,留在开封就要当亡国奴。”
“我和几个同学商量着要从家里偷跑,一同到延安。”
“国民党看见大批知识分子奔向延安,为了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在从西安到延安的中部县设卡拦截学生。西安办事处将我们一百多人编成一个护士大队,每人发了灰军服、八路臂章,我们就这样参了军,都高兴极了。因为都是没有走过长路的学生,所以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路,我第一次参加了十四天的长途行军到了延安。”
母亲是家里的幺女。那一年“简单地拿了一些衣物,像得到解放似的离开了家”,还不到16岁。
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贫家子,一个是富家女。一个属于被“围剿”的“赤匪”,一个则是名门望族的小姐。不论就哪个方面衡量,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结合似乎都是天方夜谭。
但那恰恰是一个非常的年代,一个中国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狂飙突进的年代。
父亲在自传中说:“1925年‘五卅运动’,我也同学校一道上街游行,进一步懂得一些什么(是)列强欺压中国,中国是头睡狮。”
母亲在回忆里写:“1939年,我16岁,一个欢蹦乱跳的女孩子,为了不当亡国奴,从这个大门走向了革命。”
他们本处不同地域,本属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背景,拥有不同身份。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国家状态,使他们各自舍弃家庭而投奔革命洪流,最终在延安集合成一个整体,完成了人生命运的交流汇聚。
有句哲言说:“人的一生纵然漫长,关键时刻却只有几步。”父亲和母亲在中华民族命运面临历史性抉择,民族成员或为奴隶或为英雄或为逃兵或为先锋的时刻,迈出了他们关键性的一步。他们都没有把个人命运与家庭命运联系在一起,都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父亲从江西出发到延安,万里长征。母亲从开封出发到延安,千里奔波。他们都抛开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双双成为各自家庭的“不孝者”,甚至“叛逆者”。他们又都加入了轰轰烈烈重新塑造中国命运的革命运动,双双成为黄河之滨聚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这就是如今每个周末期盼子女个个回家的年迈母亲。当她在灯下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的时候,当她推着轮椅在院子里蹒跚散步的时候,孙辈的年轻人能否想象出、感悟到这位慈祥的老奶奶波澜起伏的一生?
人生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向往是什么?得到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完全弄清楚。
唯物辩证法说: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讲得实在透彻。人人皆过客——不论多么伟大或者多么渺小。生命皆过程——不论多么丰富或者多么单纯。世界上的每一个家庭同样如此,都离不开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一过程。
明白了这些,更让人感到有必要记录下母亲及这个家庭的非同寻常之处。历史将会证明,中华民族的崛起,实际上从父亲母亲那一代面对民族危难、毅然跨出家门的时刻已经开始。
虽然我们这个家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伴随这一进程,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由衷地骄傲,因为经此非凡年代,这个家庭参与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的崛起历程。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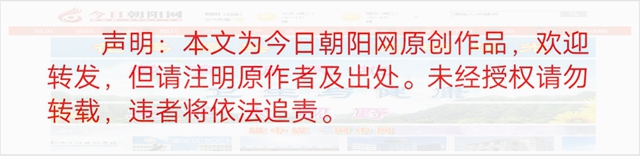
[实习编辑 关茗月 编辑 瑞雪 审核 雅贤 编审 春语]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