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四章 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写给自己
幸福是财富,苦难亦是。比它们更珍贵的,则是领悟。我们这代人生活得如此认真,尽管属于我们的春天满地泥泞。

在踉跄中完成最初的成长
真正陷入泥泞,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9年底,造反派勒令我们搬家。12月29日通知,12月30日必须搬完,只有一天时间。当时父亲已被关押两年,母亲刚刚解除监禁,大姐发配黑龙江农场,二姐分到安徽,三姐去了内蒙古兵团,大哥在陕北插队,只剩下我和上初中的弟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带着我们收拾的东西,反正家已被一遍一遍抄过,门也被一遍一遍封过,实在没有太多东西好拿。第二天一早,我们爬上大卡车,凛冽的寒风之中,连人带货一车拉到了北太平庄。
北太平庄大院里,别的家庭都在热热闹闹地买东西准备过年,我们一家如何在那个小单元中,茫然无措地完成安顿,度过60年代最后一天,迎来70年代第一天,一点儿记忆都没有。也许专案组那些人就是要用这种特殊方式,让我们记住这个“无产阶级取得伟大胜利”的元旦。
我们还获得一个最新称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他老人家给起的。“黑帮子女”还只是形容这些子女的家庭背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却指这些子女本人几乎无可救药但勉强还可以救药了。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面前,我感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黑帮子女”的杀伤力还要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自上学以来,虽然有过个别捣蛋行为,甚至还鬼使神差地逃过一次学,在外面漫游晃荡一天,但在课堂上,我却一直是规规矩矩的。三好学生、四好学生、五好学生……自幼以来得奖状无数,各门功课皆优。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当中队长,当班主席,六年级时获“特等生”荣誉。小学升初中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全部免考,直接保送上中学。当时全班近50人,成为“特等生”保送上中学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女生朱小同。别的同学紧张万分地走进考场,在一遍又一遍刺耳的铃声中坐好、发卷子、开始答卷的时候,我可以在操场上开心地荡秋千,看蓝天白云,哼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现在好了,一瞬之间成为几乎无可救药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我被学校评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9月份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刚刚排练好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1日,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组成方阵,接受领袖检阅。我们手持鲜花,根据不同信号旗举起不同颜色的花束,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就能看到不同的图案和组字。为了确保整齐划一,我们每个人都反复默诵不知讲了多少遍的特别规定:眼睛只许看信号旗,不许看游行队伍,更不许伸头张望天安门上的领导人。只有待游行结束,最后一个节目才是属于我们的。那一刻少先队方阵把所有鲜花举过头顶,一齐跑向天安门。
事前众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了,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甚至踩死,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最后这一点令我们印象特别深,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来——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我们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那个时刻令人终生难忘。我们全体少先队员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双手挥舞鲜花,一片鲜花的海洋,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当我们跑到金水桥西侧,大家的喘息、呼喊立即变成纵情的欢呼,因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正好向我们这一侧走来,一边走,一边招手。没有走到尽头,老人家停下脚步,侧过身来扶着栏杆,身体前倾,向天安门下面金水桥畔的少先队员招呼致意。
这回真看清楚了:毛主席的脸色又黑又红,微风吹起了他的头发,他微笑着,那么健康和慈祥,向我们一下接一下挥动手中那顶浅灰色的帽子。那一瞬间深深嵌入我的脑海。教室前方正中间悬挂的那幅毛主席的标准像,梦境一样化为眼前的真人!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周围几乎没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个个在流泪,个个在抹泪,个个在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毛主席万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间过去四十多年,还常常回想这一幕。那个年代已经被归入“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我们当时的行为就是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吗?一个11岁的少年,知道什么叫“个人迷信”?知道什么叫“个人崇拜”?在哪儿学的?谁强迫的?似乎并没有。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中的太阳。见到毛主席,让周身沐浴阳光,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幸福。少先队员并不迷信,人人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鲜血染成。但当“红太阳”迎面升起的那一刻,那种空前强大的磁场,让人觉得看见的确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来还是在梦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阳神。
万万没想到,不过6年之后,这些神圣的东西竟然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起因就是那场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9年4月,我和老友甘治在家中收听“九大”召开的新闻联播。当时外面街道上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俩把门窗紧闭,趴在收音机前,边听新闻边悄悄议论。如果把当时两人的话语一字一句记录下来,再拿给6年前的我看,肯定会被自己这些“反动言论”惊得目瞪口呆。
6年的变故如此之大,绝不仅仅因为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父亲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母亲多有论及,我不赘述,只补充一件事:我们家从昆明到北京,正屋中间一直挂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父亲最喜欢这幅挂轴,多次请别人来讲解,自己也亲自讲。父亲每次讲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时,眼中似乎总有泪花闪过。当时我年纪尚小,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一句,怎么讲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说“牺牲”而要说“折腰”呢?“折腰”后一定会死吗?
《沁园春·雪》大条幅旁边,还挂有两幅小一些的条幅: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父母同样不知多少次给我们讲什么叫“千夫指”,什么叫“孺子牛”。由此还生出后来的一个笑话。
“文革”兴起时我上初一,眼见别人纷纷造反了,班里几个好学生紧急商量:不能再让别人说我们是“小绵羊”,必须成立个战斗队。叫什么名字呢?我一下想起了家中的条幅,张口说:就叫“孺子牛战斗队”吧!当时大家也没什么好主意,于是一致通过。后来才明白我们犯下的错误是多么明显。
在那个盛行“造反有理”的年代,这个名字的确糟糕透顶。很快,高年级甚至同年级同学都开始笑话我们。连初二女生都成立“雄狮战斗队”了,人人在传诵红卫兵战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如此强悍的氛围下,我们竟然管战斗队叫什么“孺子牛”,不但一点儿提不起造反之气和战斗之气,反而一看就知道是一伙不折不扣“五分加绵羊”式的“老保”(对保皇派的称呼)!
战斗队刚刚降生即遭此重挫,垂头丧气的我们蹬着那辆不知从哪儿借来、总也把不稳方向的三轮车,在校内校外刷了几条标语——糨糊还是家里陈秀英阿姨帮着熬的——全部战斗活动便草草收场。四十多年过去,2008年初,老同学聚会回忆往事,一名当年的战斗队成员还在大声发问:“‘孺子牛’这名字是谁起的?”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这种家庭教育很难产生“造反派”。“文革”开始,我们全家无人热衷造反,更无人模仿当时的时髦举动,站出来“大义灭亲”,揭发自己的父母。对“革命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革命者的命”这类拐弯抹角、深奥复杂的政治斗争概念,我们这家人感到分外难以理解,分外难以实践。
自己不实践,别人就给你实践。很快,这句话应验到我们头上了。
1967年初,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次家庭会议上,爸爸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有一天我被打倒了,你们也跟党走,跟毛主席走!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坐在那里听,不以为然。妈妈却坐不住了,赶紧补上一句:当然啦,你爸爸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不会被打倒,谁也打不倒。
没多长时间,他们就双双被打倒了。这就是那个荒谬的年代。父亲一关就是5年。
这5年之中,父亲如何被诬陷、被批斗、被殴打,我不愿再重复。最艰难的时候是他身患重病自虑难愈,曾用颤抖的笔迹在一个药袋背面写下“遗书”——“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一叠好放进自己内衣口袋。他估计难再看到光明,最后也要留下自己的不甘心。这些事写多少天也写不完。
父母被关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生活拮据。我当时眼睛开始近视,急得不行,到处找地方扎针灸。那个年代针灸流行,诊所里躺着、坐着一排又一排脸上扎满银针的学生。为了治好近视,大家都对银针无所畏惧。但问题是钱。去一次收费3毛,两三天就得扎一次。什么时候能扎好,谁也不知道。三姐当时管家,为维持全家生活开支,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我三天两头找她要钱扎针灸,她脸上从无难色,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我,令我至今想起来也感激不已。
就这么点儿生活费,还须省出钱给父亲买药。我们夏天冒着烈日、冬天顶着寒风一次次骑自行车把买来的药送去,专案组那几个家伙不动声色地全部收下,后来才知道他们一次也没有转交。5年后,父亲被释放,他们把药瓶装了一麻袋,“退还”我们。真不知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儿人性。这种品性的人被“组织”信任和赏识,坚贞和忠诚怎能不像垃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踏进烂泥!
当年的这些“风云人物”,今天不少也住进干休所了。说他们能良心发现、良知顿悟、感觉悔恨,我根本不相信。人的世界观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对他们来说,“文革”前不过是本性的蛰伏,“文革”中则是本性的完全释放和彻底暴露。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文革”后,辉煌时期过去,又只好进入本性蛰伏阶段了。他们不再出声,不过是因为失去了条件和环境。他们会在那里静静地潜伏等待,等不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内心也是“死不瞑目”的。
1972年底,第一次允许我们探视父亲。让人想不到的是,被关5年的父亲竟然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认不出来了。当姐姐和哥哥相继进入那间狭小的会见室后,他指着跟在后面的我和弟弟问母亲:“那两个是谁?”
我忘记哪本书里描绘过类似囚徒与亲人相会的情节,长期关押使亲人之间相见不相识。书中的情景发生在久远以前的时代和非常遥远的国度,但现在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冷冰冰地坐在旁边监视的专案组人员看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不知是否认为这一幕也属于他们的“伟大胜利”。
父亲这一代人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无数艰辛、无数征程、无数牺牲,不顾家庭、不顾亲情、不顾个人,只为新中国和革命胜利。作为家中独子,祖母从小对他宠爱有加,倾尽贫寒家庭之所有,供他读完高小,却因他执意参加革命而倾家荡产。大革命时期,父亲在家乡搞农会,抄土豪的家,分土豪的地。大革命失败,被土豪抓住吊在房梁上。祖母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用120光洋把他赎回。人赎回来了心没回来,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祖母把他关在家里,听说红军攻克永丰县城,他从家里翻墙头跑出来,参加了红三军。祖母找到队伍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
父亲在自传中描述:“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来养老的。”他还是义无反顾跟着队伍走了。全国解放后,他把祖母接到身边,祖母已近双目失明,难以辨认思念多年的儿子了。他怎么可能想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后,轮到自己从囚禁地放出来,连自己的亲子也不能辨认。
父亲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情。越是伤心的事越不提。他不想让任何他认为不好的,可能与子女应该持有的理想相悖的东西存留于我们内心。他不提,我们也尽量回避,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正是这些留存于大脑、领悟于内心的事情,使我们真正从天真走向成熟。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我们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的变故,随后更大的冲击则来自社会的震荡。1968年底,伟大领袖发出新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连夜锣鼓喧天庆祝。“最新指示”发布之后,各学校便掀起去农村插队的高潮。哥哥是1966届毕业生,首当其冲。
1969年1月,他与一些同学结伴,报名去陕北插队。临走那天,我与几个同学混到北京站去送行。所谓“送行”,不过是去看热闹而已,看看高年级学生怎样走向社会。当时我心里很痒痒,充满跃跃欲试的冲动,也想跟着走,让哥哥好一顿说,只好暂时作罢,上车站看热闹的事也没跟他讲。
当时,北京火车站外面正在修建地铁,完全没有今天的“浅埋暗挖”技术,而是一条大路全线剖开,挖得又宽又深,建好地铁通道后再行覆盖,土层暴露面特别大。北方冬季风大,北京火车站前因此风沙漫天,尘土遍地。外面沙尘飞扬,里面激情飞扬。
当时,知青或插队或去生产建设兵团,基本都从1号站台出发,我们几个人挤进去一看,确实激动人心:打红旗的,敲锣鼓的,戴红花的,放鞭炮的,与亲人告别的,与同伴说笑的,大声喊着找人的,早早上车占座的,还有各学校此起彼伏的哨子声……真有点儿《十送红军》里唱的亲人送战士出征的景象。
找了半天,不见哥哥他们的队伍。火车已经快开了,车站的气氛开始有点儿不对,空气开始变得凝重,但大家还能把持住,相互拉手,强作欢颜。这时候,我看见了哥哥,他从列车远处一节车厢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双肘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
汽笛响了!声音凄厉,撕心裂肺。
几乎就在与汽笛响起的同时,突然像天塌下来一样,整个车站瞬间爆发出“呜——呜——呜——”似江河决堤一般的呜咽和大恸!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在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数干人像这样不约而同地集体失声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车下的哭,车上的哭,招手的哭,挥旗的哭,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有的使劲压抑着哭泣,有的号啕大哭……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那种从肺腑中迸发出来的集体悲哀,像一柄灼热的利剑,再坚强的人也会被一下子穿透。我没有上去与哥哥打招呼,站在那里止不住眼泪滚滚而下。幸亏戴着个大口罩,把大部分眼泪吸掉了,别人不太看得出来。
列车移动了,人们的哭声更激烈,潮水一样的声音淹没了汽笛声和车轮与铁轨之间的金属摩擦声。趴在列车窗口的哥哥眼圈红红的,竟然没有哭。他真够硬,我佩服不已。
后来又有过无数次送行。送三姐、送董春生、送肖淮河、送甘治……每次送行都像全体约定好了一样,列车发车前汽笛一响,车站就会发出那种整个站台为之颤抖、让人灵魂惊悚的恸哭。没有到现场听过的人们,永远想象不出那种声音给人以怎样的冲击和震撼。
后来很多人回忆“文革”时说,听到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行了。我却不是这样。1969年北京车站送行时,那种渗入骨髓的集体大恸,已经聚集了足够的能量,让人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场“革命”无论表面怎样轰轰烈烈,其内核已经开始在普通大众内心的潜意识中被摒弃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心里说的话与嘴上说的话,差异竟如此巨大。虽然在非常时期,人们披露心声的时间那么短暂,但也足够了。它对我的启示之大,难以言表。有些人的成熟需要一生,有些人的成熟只需一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就白了头。我相信关内的伍子胥与关外的伍子胥,必定判若两人。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知使多少人“史无前例”地迅速成熟。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想,早晨醒来想,拿着铝锅去打饭时想,从北太平庄宿舍向西走,坐在残破的元朝城墙遗址上也想。这是我的精神炼狱。
从蓝天白云的国庆节、高举鲜花跑向天安门的优秀少先队员,到抄家封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黑帮狗崽子”,再到尘土遮天、哭声撼天动地的北京火车站,以及后来当工人所在的那个漆黑如锅底的瓶底管车间……
我在踉跄之中完成了成长的最初轨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教育好了——不是用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而是用钢铁一样冰冷的社会现实。我们这些被誉为“生长在蜜糖罐里”的一代,从被砸碎的蜜糖罐里集体摔出来,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艰辛和双重磨难之中,不回头地走上了各自的成长道路。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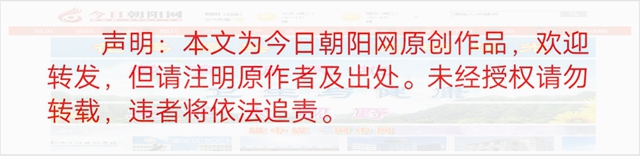
[实习编辑 关茗月 编辑 瑞雪 审核 立军 编审 春语]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