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四章 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写给自己
幸福是财富,苦难亦是。比它们更珍贵的,则是领悟。我们这代人生活得如此认真,尽管属于我们的春天满地泥泞。

恶劣环境中的一方净土
北京东单公园斜对面那个黑如锅底的瓶底管车间,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个驿站。那里的大爷大妈、那些淳朴的工友和同伴小景、小童、小冯抚平了我的愤怒,缓解了我的伤痛,让我展开了奋斗的空间,让我看到社会和人性的另一面。今天想来,对他们不知如何报答。
其实我对首都北京毫不留恋,早想远走高飞,无奈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连个愿意收留的单位也没有。1968届学生开始分配,先是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不让去,可能是怕离边境太近“投敌叛国”吧。随后是嫩江国营农场,也不可以,理由基本同前。眼见新老同学一车又一车奔赴全国各地,自己却在那里“待分配”,心中万分焦灼。于是决定自己找插队地点,与老友甘治一起上河北晋县投奔他的老同学。
那天在晋县下火车后我们徒步40里,生平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途中问老乡无数次,得到的回答都是“还有十几里”,把“十几里”弄成了一个让人盼不到头的概念。天黑之前终于疲累不堪地走到那片村庄,老同学的接待十分客气,又做饭又烧水又聊天。第二天上午和下午我们把周围环境细细考察一番,心里有了点底。摩拳擦掌正准备在这片广阔天地牢牢扎根大有作为,失望又一次接踵而来。
晚饭后,甘治的老同学用缓慢、沉稳、委婉的男中音字斟句酌地说出了他们的集体考虑:来人已经够多,无法再接受新人加入。
这一最新打击未使我们更加麻木,因为我们已经足够麻木了。甘治悄悄告诉我,看见他们一个个男男女女都已成双成对,就觉得我俩可能多余。现在果然如此,只好走人。
我们是第三天上午被他们用自行车送回火车站的。
火车到北京,出了站台各自取自行车,昼夜存车处的人说你俩先等一等。这一等等来两个民警,不由分说把我们带进北京站派出所。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的自行车存了三天两夜,存车处的人认为我们很可能是到外地流窜作案,于是向派出所打了报告。那个年代就是如此,人们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一个比一个紧,到处都在告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我们被分头审问。开始我还理直气壮地辩驳,那个老民警一个问题就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包里是什么东西?”
包里是一只活鸡,在晋县火车站买的。我和甘治一人买了一只。一是因为不能白去一趟,怎么也得有点儿收获;二也是因为确实便宜,想买回来改善伙食。现在可好,撞枪口上了。只要查出你从外地弄回只活鸡,给你安个“长途贩运”或“投机倒把”的帽子,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当时已经没有退路。我后脊梁出汗,硬着头皮回答说:“一包衣服。”“真的是衣服?”“真的。不信你翻。”
其实哪里经得住翻,只要上来一摸,就一切完蛋了。
老民警没有上来。
只要那只鸡动弹一下,更别说再“咯咯”一叫,谎话就被揭穿了。
但那只鸡也没有叫,甚至没有动。
太争气了!关键时刻!
电话铃突然响起。冥冥之中,好像真有什么力量在暗中帮助我。老民警一边接电话,一边不耐烦地对我说:“好了好了就这样,可以走了,以后在学校听从分配,少到处瞎跑!”
我故作镇静地从派出所走出来,把自行车推到安全地点,再打开包看那只关键时刻的“争气鸡”。
鸡已经闷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一点儿不知道。
不久,甘治带着他得意时晃晃悠悠的劲儿也走了出来。他经历的过程几乎与我一模一样。
结果竟然也完全一样:他包里那只鸡也闷死了。
河北晋县这趟“历险”过后,不死心的我们又联系过河南罗山、光山等几个地方,皆是徒劳,全部失败。
后来甘治自己走了——他弄到一个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名额。临走前他告诉我:再不走实在不行了,刚刚解除监禁的父母已经在“求求他赶快找个地方落脚”。我至今记得甘治告诉我这一情况时,那一脸痛苦的表情。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其父母要“求”自己的儿子早点儿离开。
我所面对的现实十分尴尬:所有同学全部走光,只留下我一人,像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弃儿,待在被遗忘的清冷角落。
妈妈从石家庄干校赶回来,一趟一趟去学校,找工宣队,找军代表,陈述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知付出多少努力,终于使学校同意分配我到工厂。
所谓工厂,不过是个街道小厂而已。20名分配到该厂的学生中,其中3名“成分”最差:“黑帮子女”的我、奶奶是法国人的小冯、父亲是资本家的小x(女孩,忘了姓名)。于是我们三人被送到瓶底管车间报到。
就像1969年初我惊呆在北京站送行的人群中一样,1971年初,我惊呆在东单公园斜对面那个简陋和糟糕到可怕的瓶底管车间前:约40平方米的车间内,四壁被煤油灯熏得漆黑,大白天进去,眼睛好长一会儿才能逐渐看清室内布局——两条长长的木桌上,四排煤油汽灯在鼓风机作用下吐着蓝色火焰,工人们坐在长桌两边的木椅上,急速转动手中一节节玻璃管,烧制装阿司匹林药片的药瓶。一张张脸分不清男女,都是鼻翼灰黑、满头淌汗、面颊被高温煤油汽灯烤得通红。
我和小冯、小x呆呆地站在车间门口。新中国还有这样的工厂,还有这样的工作场景,与“社会主义是天堂”的认知大相径庭,与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在宣传画上看到的,天壤之别。
又停了一会儿才看得更清楚:近30个工人师傅中,年轻人极少,几乎清一色是老大妈。
帮我们完成安顿的是车间里唯一的男性——比我大七八岁、从少管所放出来的小童。接着更为细致帮忙的是另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幼儿师范毕业的女工小景。我们进去以前,车间里只有这两个年轻人。
毕竟成熟些了,这一轮震惊和犹豫对我来说十分短暂。事实明摆着:作为“黑帮子女”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不来这里谁来这里?如果姐姐不上内蒙古兵团、哥哥不去陕北插队,你想进街道小厂都进不来。现在除了好好干、玩命干、珍惜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哪里还有挑肥拣瘦的权利?
这个烟熏火燎的车间,成为我走上社会的最初起点。小冯、小x、小童、小景,成为我走上社会的最初同伴。
也许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小冯、小童和我,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每次工间休息,我们三人都要从煤油味呛人和鼓风机震耳欲聋的车间里跑出来,坐到马路对面东单公园的铁栅栏下,抽烟聊天,谈天说地。
小童来得早,又是当时车间唯一的男性,分配的活是全车间最好的:戴着线手套,把长长的玻璃管一节节切下来。我和小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必须上煤油喷灯工作台,坐在大木凳上拿着那一节节玻璃管烧制药瓶。
老师傅们手把手教,我也专心致志地看和学,整天反复琢磨为什么我烧的瓶子先是封不了口,能够封口了瓶底又呈锥形而站立不住。当我第一次烧出一个底面勉强够平、勉强能够站住、勉强算合格的瓶子时,简直无比兴奋,长久以来第一次品尝到成功的滋味!
最初垂头丧气的小冯受我情绪感染,很快也认真学起来。年轻人都不服输,我俩开始较劲和比赛:看谁烧得多,看谁的瓶子质量好。短短一两个月,我俩烧成的瓶子就从最初的十几个到几十个、几百个,然后上干,直到最后一天能烧两千多个。两人天天也是鼻翼灰黑、满头淌汗,面颊被高温煤油汽灯烤得通红,与周围工人师傅毫无二致。
后来听说厂里预先已有准备:这几人在瓶底管车间待不了多长时间肯定闹着要走,正好顺水推舟把他们退回学校——工厂本来还不想要这些人呢!厂领导没有想到,这几个家伙不讲条件,干得还挺来劲。车间师傅们也笑逐颜开——单纯的年轻人不仅带来了活力,还带来了干劲。大家都说小金、小冯这两个小伙子干得真好!
也是短短一两个月时间,我双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指尖都开始变白。这是烧瓶子时离高温煤油喷灯很近、需要反复转动玻璃管的几个手指。开始感觉指尖被灼烤得难以忍受,后来就渐渐麻木了,再后来指尖开始慢慢发白,回家端刚出蒸锅的滚烫菜盘都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指尖的末梢神经被烧死了。
当我带着几分炫耀专拣最烫的盘子端,以显示自己不怕烫的能力时,能看出来妈妈的难过。从小在家我就是个很少做事的人。妈妈指挥姐姐、哥哥和弟弟干这干那,却很少让我去做什么,只要抓紧学习就行。现在看到我整天穿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天不亮就赶头班车去上班,天黑透了还不能下班回来,与过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准南辕北辙,她的心情可想而知。
妈妈很难受,我却很得意。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又是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在人们认为是社会底层的这块地方,没有没完没了的斗争,没有势利的白眼,没有身份的歧视——对“黑帮子女”的我,对1/4法国血统的小冯,抑或对从少管所出来的小童,都是如此。只要好好干,就有人说你好,就有人关心、体贴和爱护你。它的环境恶劣,却又是一块净土。
“哎呀,小金当心,不要烫着了!”普普通通一句话,像甘露一样滴在自以为已经坚硬如铁的心上。当我带着浑身愤怒、满心伤痛和不假思索走向社会之时,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社会上还有这么多善良的、从不伤害别人的好人。我的心是被这些朴实的工人师傅、大爷大妈和周围同伴们焐热的。
当时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不管干什么都义无反顾。
工厂要组织人到石景山钢铁厂搜集废铁,那是个有风险的粗活重活。别的车间不想去,我拉着小童、小冯三人一起代表瓶底管车间报了名,还生怕厂里不批准。到石景山钢铁厂的炉渣堆场一看,好拣的废铁早被其他工厂弄光了,于是炼铁厂拉炉渣的车皮一过来,灼热逼人的炉渣刚倒出来,我们冲上去抡开铁锤就砸。滚烫的炉渣四下飞溅,工作服烧出了窟窿、皮肤上烫出了白点,也咬着牙全然不顾。其他厂来捡废铁的人们围在一旁议论:哪个厂来的野小子,见铁不要命啊?!
事后想想也的确危险:如果炉渣溅到眼睛里,麻烦真就大了。当时就是用这种不管不顾的蛮干,来表达心中对我们那个街道小厂和周围师傅们那份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和这些人相处,我觉得格外的亲。
车间四十多岁的房师傅在拣废铁现场负责后勤,太阳烤得她炎热难耐,拿块湿毛巾顶在头上,手里攥着冰块。我看见她就说:“啊呀,房师傅我渴死了,冰块给我吃吧。”她很吃惊:“你真要吃啊?”我说当然要吃,接过来一口就吞了下去。
后来房师傅几次在车间会议上说这件事:“你看看我们分来的学生多好啊,我那个冰块在手里攥了半天,人家小金一点不嫌脏,一口就吃进去了。”这是一种完全不设防的信任。脏不脏这概念在脑子里连闪都没闪过。
在瓶底管车间,对我关心照顾最多的人是小景。从进车间那一刻起,她就像个大姐姐,给我铺好工作台,给我换合适的凳子,又帮着调好煤油喷灯,然后耐心细致地告诉我烧瓶子的操作要领。每每被高温喷灯烤得口干舌燥,我都会发现旁边有她放的一杯工厂自制的冰镇汽水。
我们来之前,车间里只有她和小童两个年轻人。小童是车间里唯一的男性,因少管所的经历变得沉默寡言,干活时缩在车间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切玻璃管,开会也是尽量待在光线最暗的角落不发一言,黑黝黝的他像个几乎不存在的隐身人一样。小童的这种精神状态,使性格开朗、敢说敢做的小景,在这个以老大妈为主的车间里,几乎找不着可以交流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互相感染和传递的。后来小景讲,如果我们不来,她很快也要被闷老了。
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们那种不知苦、不知愁、不知累、乐观向上的情绪似一股清风,首先感染了小童。他变得话多了,爱谈笑了,干什么事也不再蔫蔫地随后尾,而是愿意跟我们一道去积极争头排了。
然后感染了小景。甚至可能最先被感染的就是她。她开始加入我们三人的小团体,工休时毫不顾忌性别差异,与我们凑在一起谈天说地。随后又像个男孩子一样,要求与我们一起去石景山抡锤打铁,没被批准,就要求与我们一起去挖防空洞。
“深挖洞”是一项完全不适合女性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要在很深的狭小洞内把土一锹一锹扬上去。她没有那么大劲,憋个大红脸艰难地往上举铁锹。我们怎么劝她上去都不行,一定要坚持干,说“跟你们在一起快乐”。干重活的人饭量都很大,她回回觉得我没吃饱,当我吃完自己那一份后,她一定要把她饭盒里的鸡蛋炒饭再分给我一半。看着我吃,比她自己吃不知高兴多少倍。
那段日子里,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成了“黑帮子女”,我也不会问小童为什么进了少管所,不会问小景为什么没有如愿当上幼师而来到瓶底管车间。我们这些同伴之间,家庭、年龄、身份,甚至性别的差异似乎都不存在。连最初眉头紧蹙、心事重重的小冯,后来也无所顾虑地跟我们讲他法国奶奶的故事,还有他那同样因身份倒霉遭难的父亲。
在那个人人相互防范的年代,我们却拥有一个彼此信任的交流语境,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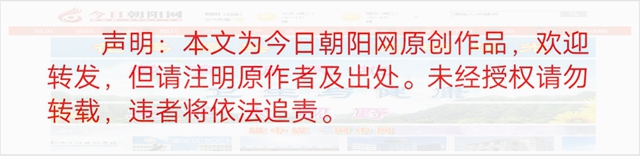
[实习编辑 关茗月 编辑 瑞雪 审核 立军 编审 春语]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3(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2(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1(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10(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9(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8(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7(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
《心胜Ⅲ》006(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