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念一匹马
文/梁清玉(辽宁凌源)
2020年11月5日傍晚,我忽然间变成了父亲的“大妹子”:他不认识他的大女儿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有几个子女,连我的母亲也不认识了。我知道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但是不应该是今天。
三个多月来,每天下班,进屋换鞋,不敢洗手,就要先摸摸爸爸的额头,感受一下他的体温。七月份时,爸爸肺炎发烧抽搐惊厥,120接入医院急救,真真吓坏了我们。
爸爸耳聋了,多大的声音都听不好。每次和他说话,他都是打着超级离谱的岔子。在无声的世界里,他该有多么的寂寞和孤独!
爸爸曾经做了二十几年的赤脚医生,是识字的。我买来记号笔,用最常见、最直白、最土气的词句,在纸上和他说话。有时,还要不惜写上一些让我这个语文老师最最深恶痛绝的错别字,只为让他会读,读出音来,尽管,每一个音都是那样的含糊不清。
爸爸有时情绪非常激动,难以沟通。尽管之前给他写了“打针呢,不能乱动啊!滚针了还得再挨扎呀”,那一天,他还是拔了三次输液管。
氨溴索口服液和血康口服液,我想,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最难喝的药了。因为喝了两天之后,父亲就再也不肯喝了。他把嘴闭得紧紧的,用手死死捂住,再用被子蒙住,说啥也不肯喝。这真是难住了我。望着虚弱的爸爸,真的不忍心掰开他的手和嘴硬灌。
“不管咋样,这药可得喝下去。”老姨说着就用汤匙撬开了父亲的嘴,直接就把药灌下去了。父亲生气了,皱着眉头,撩开被子,用手指着老姨大声嚷嚷道:“你咋这么折磨我呀!”回手时把我给他写的那一沓带字的纸打到了地上。病友们和陪护的家属都被他的孩子气逗笑了。
然而,笑声是他们的。置身其中,我又怎能笑得出来呢?只有无奈与心疼罢了。一张一张地捡起字纸,忽然间,一道灵光闪过,一条妙计完美催生。
晚上,他仍旧拒绝喝药,并伸手把药瓶打在地上。我捡起药瓶,拿出了写着“这药100块钱一支,你要是不喝,100块钱就白瞎了!”的字纸给他看,他睁大了眼睛,用含糊的语音大声说“唉呀!那可了不得啊!100块一支,也—忒—贵—呀!”然后,就非常乖、非常主动地一口把药喝了下去。尽管药依然苦得他呲牙咧嘴,但是,以后每次喝药却顺理成章的痛快。
爸爸偶尔也有思维清晰的时候。九月份,送女儿上大学回来,他问我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并且像个委屈的孩子似的告诉我:“你不在家这两天,我头疼了!”我一下子捧住父亲的脸,忽然间就想哭。“父母在,不远游”的意义,在那一刻体会得最深刻、最透彻。我告诉他,孩子高中毕业上大学了。他眉开眼笑地说:“你这是把孩子供出来了!”我在纸上写道:你高兴吗?他竟然笑着把我的名字唱了出来,唱了两遍。
每晚睡前,亲吻他的额头,他咯咯地笑出声来:“这破爸,还这么稀罕呢?!”“我大妹子真好看!”我做着“睡觉吧”的口型,挥手拜拜,示意他我要关灯,他像个听话的孩子,点点头。
然而,爸爸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的作息,已经完全黑白颠倒了。他大声地叫着他的父母,叫他兄弟姐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说着那些陈年往事,在床上打转,抓住床栏想起却起不来……一个又一个的沉沉黑夜,他非常专注地投入到慷慨激昂的演讲中,又自导自演着一场高难度的独角马戏。
星汉西流,夜色渐淡,折腾了整个晚上的他,终于甜甜地睡着了。他就在我的面前,一尺之遥,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夜我竟然特别地想他。俯下身子,仔细端详他白眉灰发、沟壑纵横的沧桑,发现有些想念总是刻骨铭心。想他三更早起赶着马车上路,一挂马车一路叮当的驼铃,向着黎明,欢快而响亮的吆喝声和“叭叭”的鞭响;想他那匹马;想他半夜被病人家属喊醒,忽地一下跳起,披衣飞奔出诊的高大背影……
那年我高二,秋风里,父亲跋涉二十余里山路,为神经衰弱的我求医问药。周末返校,我呆立在车站,焦急地等待父亲买药送来。许久,远远的,落日的余晖中,秋风撕扯着他那过早灰白的疏发,满头凌乱。他边飞速地蹬车,边扬起提着药包的手频频朝我挥舞。我知道他是在告诉我:药来了,你的病很快就会好了;你放心,不会耽误你上学的,爸爸心里有数!这频频挥手的经典瞬间,与三十年后他目送我回程的动作何其相似!
父亲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左腿行走困难。没有极特殊情况,每周末我都要去喀左看望。每次我要回程时,父亲都要拄着拐杖,两步一个台阶,走13级楼梯提前下楼,去平台上等着送我。我呢,每次走到楼头拐角处,都要停一下,挥挥手,看到父亲也挥挥手,再匆匆离开。又一个周末,我急匆匆地去赶午后六点的末班车,竟然忘记了挥手告别。当时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80岁的父亲和我是不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最后的一次挥手。走出大约100米远,我突然又折了回来,惊奇地发现父亲还痴痴地站在那里眺望。我马上挥手致意,只见我那耳聋眼花的老父亲竟然凭着感觉也挥起手来。我的脚步再也难以移动。可是,百里之外的明天,我的女儿还要上学,班级里的45个孩子还在等着我上课。古人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而此刻,站在忠与孝之间的我,是忠孝两不全啊。
然而,这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当年强壮而勤劳的父亲如今却只能卧床度日了。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小脑萎缩虽然导致父亲稀里糊涂,但是潜意识里他的农民本色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那块山坡地得坐水种啊,地太旱,出不好苗啊”“赶紧收茄子辣椒,今晚有霜冻”“咱这马得打预防针了”……
记忆从未走远,那匹马瞬间在我的脑海中疾驰而来。那匹马,高,壮,通体雪白,英武俊俏,性格温顺,脚力好,活计好,种地拉车,无所不能,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父亲忠实的朋友,贴身的侍卫。寂寂寒夜,凛凛清晨,一个农人,一匹白马,一串鞭响,一路驼铃,追赶日月星辰。
那天,一袋粮食突然从车上滑落,父亲一个急刹跳下车去,糟糕的是,右脚却套入闸绳,被拉倒在车底下。当时车上载着两千多斤粮食,如果轧过来,父亲有可能受重伤甚至性命不保。千钧一发之际,那通灵的老马竟然拉着车绕过父亲的上身,车轮只从腿上压过,虽然腿上的肌肉被轧出一道青紫色,但是父亲平安无事。从此,父亲的鞭子再也舍不得落到马背上。
历经十年之久,马老了,贫困的家庭却养不起它了,需要给它另寻一个推碾子拉磨的人家。父亲把缰绳交给买家之前,再次郑重地问道:“兄弟,老哥再问你一遍,你一定要说实话呀:你买它真的是为了家用?兄弟,你必须答应老哥,一定不要卖给汤锅(汤锅,就是屠宰场)!否则,我立马反悔不卖了!”待买家再三诚恳地保证遵守诺言,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目送他牵马离开,而父亲却跟在后面,送出五六里地。回到屋里,一家人默默无言,趴在炕上悄悄落泪。整个午后,都没有下田干农活,晚饭也没有吃。
从此,三更有梦,我的白马夜夜归来。
尽管父亲思维混乱话语糊涂,却无时无刻不给我以教益:人真的不能失信。有一件事父亲梦中醒着始终念念不忘:他当年赶着马车走村串户卖米面时,有个叫王某珍的人,买了父亲的白面,欠20元钱一直没给。父亲不是小气的人,他为了亲人朋友甚至对陌生人都可以倾囊相助,但是对这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20元钱,对于有三个孩子读书的贫困家庭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巨款”啊!
今夜,五十年的岁月,就像梳子一样从心头梳过。忽地,父亲一句清晰响亮的梦话“赶紧起床吃饭啊!上学要迟到了”划破黎明前最后一丝黑暗,阳光也就在那一刻跳进窗来,照进父亲的梦里。窗外,鸟鸣虫嘤,汽车轰隆,上学的呼朋引伴,上班的步履匆匆。我想,应该还有梦中的父亲,和他年轻的白马,一路叮叮当当铿锵的歌声……
小链接梁清玉,辽宁凌源人,1995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喜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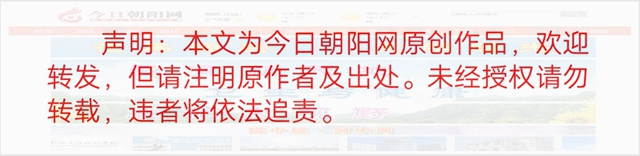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立军 编审 春语]







 由“不材之木”想到的(孙玲玲)
由“不材之木”想到的(孙玲玲) 曾向青山行(邹世昌)
曾向青山行(邹世昌) 春天里的第一张单饼(孙玲玲)
春天里的第一张单饼(孙玲玲) 春三月(孙玲玲)
春三月(孙玲玲) 海燕,我的超级搭档(杨秀兰)
海燕,我的超级搭档(杨秀兰) 落墨时光 抒情三月(辛秀玲)
落墨时光 抒情三月(辛秀玲) 总有一片雪花为你而落(邹世昌)
总有一片雪花为你而落(邹世昌) 人生独处是清欢(孙玲玲)
人生独处是清欢(孙玲玲)